
祭奠汶川地震中死难的家属(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5月14日讯】一
汶川地震10周年。那场灾难改变了很多个体的命运,也牵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新闻媒体在震后的信息传播、人文关怀、责任追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观察中国媒体的一个经典案例,尤其是观察媒体与政府是如何互动、过招的。
去年,我的朋友和论文合作者、佐治亚州立大学助理教授Maria Repnikova(我叫她“玛教授”)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媒体的好书《Media Politics in China:Improvising Power Under Authoritarianism》,其中就有一章是专门写汶川地震报道的。
玛教授的博士是在牛津大学读的,她当时拿着著名的“罗德学者奖学金”(就是那个近两年在中国被包装成“全世界最难申请”的奖学金)去了英国,不过读博期间有相当多的时间在中国,研究中国的记者和媒体。我常说,她认识的中国媒体人可能比我认识的还要多。正是因为长期在中国,并且和大量媒体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所以她对中国媒体的观察是相当准确、深入的。
《Media Politics in China:Improvising Power Under Authoritarianism》这本书是玛教授基于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完成的,由最好的学术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下,我基于这本书第五章《Critical Journalists,the Party-state and the Wenchuan Earthquake》的内容,和大家一起复盘汶川地震之后的中国媒体表现。
二
汶川地震发生后,政府一开始是不愿意进行更多的信息公开的,立即下达了严格的禁令,禁止绝大部分媒体派记者前往灾区报道,只允许采用新华社的稿件。但是后来很快就开放了一定的报道空间。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从记者这边来看,地震发生后,来自全国的很多记者就立刻奔赴灾区,其中包括新华社和CCTV等官方媒体的记者。实际上,在禁令来到之前抢着赶往现场、试图赢得报道的机会,已经成为中国记者的一种常态,更何况是如此罕见的巨大灾难。“跑得比谁都快”,其实是对记者的一种巨大赞美。当跑得快的记者们都已经纷纷赶到现场,禁令实际上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更重要的原因是,从政府这边来看,一味禁止看上去已经不是最好的选择。当时虽然还没有微博微信,但是地震相关影像很快就被网民上传到优酷等平台,比新华社的消息还快。针对灾难的禁令很可能严重影响政府的声誉。当时正值一个特殊的时间点,西藏314事件之后、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国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非常在意自己的国际形象,如果因为封禁地震报道而破坏国际形象,或许会得不偿失。
而且,如此巨大的灾难,实际上也不是政府能够独自对面的,它需要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才能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这时媒体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
因此,在一两周的时间里面,宣传部门没有下达禁令,只是要求多做正面报道。媒体关于救灾行动的报道,也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政府的形象。实际上,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市场化媒体,它们最初的报道重点都是救灾行动(展现了国家能力)以及情感上的团结(“我们都是汶川人”、“中国加油”)。政府和记者的合作关系比较顺畅。
也正是在那两周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优秀报道的产生,比如《南方周末》的“汶川九歌:大地震现场报告”特刊(5月22日)和“大地震现场再报告”(5月29日)。同时,我们也看到地方政府和NGO进行了很多合作。
然而,这种蜜月期是短暂的。很快,一个核心问题就显露了出来:校舍质量问题。官方媒体将发生在学校里的悲剧描写成天灾,但是《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财经》等市场化媒体对校舍质量及其背后的政府责任进行调查和问责。当然,这种问责其实也是小心翼翼的,因为中国的媒体在避开红线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他们将监督更多地指向了地方官员,并且更多强调“建设性”:如何让校舍更加坚固。
面对部分批评性记者的监督,政府这边是如何作出回应的呢?玛教授说,政府采用的是一种“创造性的妥协”。
一方面,政府下发禁令,禁止媒体继续报道校舍安全问题,防止这一话题在舆论中继续发酵。在这个过程中,四川省的宣传部门积极运作,既向中央请求下发禁令,又和广东省的宣传部门联系,请求支援。这样一来,南方报业的后续报道基本就被压下去了,但《财经》杂志仍然在6月9日刊出了封面报道《校舍忧思录》,这主要是因为《财经》杂志的主管单位是“联办”,不受省级宣传部门的约束,有更大的报道空间。不过,他们在这一期之后也选择了暂停追问,这更多是一种主动的策略选择,因为他们觉得继续追问的话会破坏和中央层面的关系,影响今后做更多监督报道的空间。
另一方面,政府并没有无视校舍质量问题,而是迅速采取了政策行动,比如在全国范围内提高校舍质量标准,同时释放信号:在灾区以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速度和能力重建安全校舍。
一位《南方周末》记者在接受玛教授采访时说,汶川地震后一年,他重新回到灾区,发现那里大部分学校都重建得非常好。“我想官员们是在媒体监督和公众压力之下作出这种回应的。”
然而,政府在修补校舍质量的同时,拒绝了对官员的进一步问责。因为政府不希望因为这样的事件影响政治稳定。而这实际上又导致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暴露出新的问题。
从这样的互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将政府视为严格的言论审查者,还是将记者视为一往无前的抗争者,都是不恰当的。双方实际上是在上演一场没有脚本的即兴对手戏,政府一开始严格限制,很快进行了妥协,之后又加强了对校舍安全问题报道的限制,但与此同时着手解决着校舍质量问题;而记者则是在突破、妥协、寻找安全角度、进行建设性监督等做法中游移。双方的很多做法都是临时性的、具备灰色空间的。最终的结果是,解决了一些实际的问题,但又留下了其他的隐患:表面的问题解决了,根本性的、系统性的问题却还在。
三
汶川地震的报道案例正是体现了中国媒体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玛教授的书中展现的是:这种关系远远不是那种脸谱化的、黑白分明的论述,无论是政府还是记者都比“打压-突破”这种二元关系更复杂,而双方之间的关系也非常丰富和微妙。
她认为,这种关系是流动性的,其核心特征可以被称为“有限度的即兴互动”(guarded improvisation)。也就是说,双方并不是严格按照某种事先写好的剧本来行动,而是在互动过程当中不断进行着临时的、即兴的调整。
在政府这边,党政官员允许记者进行有限度的监督,扮演一种提供咨询建议的角色。不过这种角色又是模糊的,政府这边随时可以进行修改乃至收回。
在记者这边,他们会利用对政策的重新解读,绕开某些限制,创造出进行监督报道的空间。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也是因为这些政策本身是有模糊性的,是有腾挪空间的。
当然,这种即兴的互动是有限度的,是基于由政府设定的基本游戏规则和基本政治结构来运行的,不能逾越红线。玛教授认为,记者和政府双方实际上是在同一个政治框架下行动,他们也分享着同样的目标,那就是提高治理水平。(所以,那些声称南方系记者是“反对党”的人,完全没有搞清楚情况,完全是在用阴谋论的思维臆想。而胡舒立被《纽约客》引用的那句名言颇为恰当:“啄木鸟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让它长得更直。”)
这并不是说记者没有抗争精神,而是要强调:记者和政府其实不是针锋相对的对立关系,并不仅仅是一场猫鼠游戏。实际上,他们的关系既有对抗的成分,更有合作性的、协商性的、即兴调整的成分。
之所以会是这样的关系,原因在于学界所谓的“碎片化的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中国的体制并非铁板一块,比如中央和地方之间实际上是有缝隙的,而地方官员往往成为中央官员和记者共同针对的对象。这种碎片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体制的韧性和活力,因为它有更多的灵活性,有更大的试错空间,有更多的咨询、协商元素。威权并不意味着没有参与、没有监督,只不过这种参与和监督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进行的。
当然,10年过去,当年的那种互动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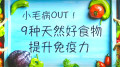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