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岩画(williamhill官网
配图)
【鉴于自焚藏人已逾百人,现将袁红冰先生所著《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在网络刊载,以表达对自焚藏人的声援与敬意。 ——《自由圣火》编辑组】
第二章 人类进入精神危机的暗夜
——东方需要自由的拯救,西方需要拯救自由
金圣悲决定作一次以当代人类精神危机为主题的哲学沉思。为此,他选择了一个神圣之地——对于哲人,思想意味着庄严的精神苦修或者高贵的心灵事业。金圣悲重返阿里,在一个可以遥望岗仁波钦峰的断崖下,他像苦修者般盘膝端坐,准备开始思想。
金圣悲之所以要在对岗仁波钦的遥望中思想,并非由于众多东方宗教都将这座圣山视为世界的中心,也不是由于在这里他获得了从梅朵芬芳的骨肉上腾起的红焰之心,而只是因为从这个方向望去,岗仁波钦宛似安放在血色祭坛上的雪白的太阳遗骸——白雪覆蓋的死去的日球,那似乎是对人类终极命运的预言,而关于精神危机的思想,在心灵的意义上也具有终极性。
“人类万年历史间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一个人口仅六百万的藏人族群,竟很可能会对数十亿人构成的人类的精神命运产生重大影响。或许只有古犹太原初的宗教精神曾经有过如此巨大的心灵能量。”
“对于近现代西方,奔腾在万里蓝天之上的西藏冰峰雪岭,意味着神秘的诱惑。睿智的康德相信,西方文化圣洁的魂,还存留在西藏高原。狂热的希姆策则试图从雪域高原上寻找“金发碧眼”的高贵猛兽的人种源流。对当代文化失望的西方文人幻想出的“香格里拉”胜景,仍然令人感到柏拉图“理想国”中等级制度的阴影。由于穷尽了世俗物欲的享乐而无聊的当代西方男女则想从西藏找到新的生命刺激,只是他们充满渴望的眼睛能找到的,只有浅薄的好奇感的满足,因为,寻找意义需要丰饶的心灵… … 。从哲学大师到普通的游客,从政治家到研究西藏的学者,他们对西藏的希冀或者渴慕,基本是从种种精神的空虚中涌现的幻想——精神空虚者总试图通过幻想,超越枯燥乏味的现实命运。
但是,西方并不了解西藏。在精神的意义上,西藏是西方文化主宰的时代中残留的一片东方文化的金霞。达赖喇嘛引领数十万藏人走上现代民族大迁徙和精神流亡之路,藏传佛教由此免于被共产专制铁幕窒息,从而为东方文化保留下一支血脉。精神危机是危机之王,它比伏尸百万,血流千里的战争、灾难或者其它社会危机更深刻地质疑生命的意义。当代人类精神危机的来临——属于西方文化主导的时代的危机,再一次逼问人生存的价值根据。这个逼问使东方文化复兴成为可能,而藏传佛教关于心灵的学说,很可能有机会为人类精神的拯救,提供生命意义的启示。所以,为探寻西藏灵魂,我的思想不得不首先走向当代人类精神危机。”
“时间虚化历史,然而,活在时间中的所有现实进程,又都能从虚化的历史和古老时间废墟中,找到真实的原因。以近代史为起点的数百年,是西方文化的狂飙突进,并终于主宰人类命运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在表述东方文化一溃万里,退出历史中心,甚而濒临灭绝的悲剧。当代历史的主题并不是如亨廷顿的学术谎言所确信的那样,由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构成。因为,东方文化的生存都只意味着昨日飘落的残花,根本没有能力同凯歌高奏数百年的西方文化抗衡。”
“当代历史的主题,在于西方文化的自我否定,自我冲突;从本质上审视,是西方文化的自由、法治、人权传统,同复活的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之间的生死决战。而人类精神危机也意味着西方文化的危机。”
“西方文化发端于两个智慧之源,即古希腊智慧和古犹太智慧。古希腊英雄史诗的泛神论,为古希腊文化确定了精神多元的自由意识。自由,乃是古希腊智慧之魂。她决定了古希腊文化的多样性的丰饶;古希腊文化因此表现为哲理、美学、正义之学的众神的圣殿;古希腊智慧不承认唯一绝对的真理,就像她拒绝接受一神论。源于两河流域的古犹太智慧是一种宗教智慧。人类需要终极心灵安慰的认知,使古犹太智慧在对于人类根本宿命的理解上,达到某种极致。不过,古犹太智慧中涌现的一神创世的绝对真理观,却在古老的年月中,就为以神圣的理由绝对控制人的心灵与肉体的极权主义,创立了基本的精神原则。绝对一神论,以及相应的真理一元论,乃是流淌在西方文化一个源头的血河。属于不同的时代和族群的三个上帝先后从那条血河中沐浴而出。犹太教上帝、基督教上帝和伊斯兰上帝,这三个都自称唯一的绝对之神间两千馀年的爱恨情仇,构成西方历史的情感动力之源。而极权主义从古犹太智慧的宗教精神原则演进成坚硬的政治存在和完备的文化传统,则是在欧洲中世纪。”
“从古犹太智慧获得灵感的基督教,创立了一个足以感动千年历史的形象:头戴荆棘之冠,为救赎苦难的人们而被钉上十字架的基督。为拯救人类苦难承受酷刑的利他主义和大爱之情,使基督的荆棘之冠升华为道德的王冠,十字架上比罂粟花汁还殷红的基督之血,则控诉着古罗马帝王的暴虐。不过,命运很快就证明,荆棘的道德之冠比黄金铸成的王冠更具历史的感召力。古罗马皇帝不得不在基督精神前低下头颅,基督教被奉为古罗马国教。”
“命运似乎总是在给予高贵权力的同时,收回道德的魅力。基督教以国教的名义与世俗的专制权力结成神圣同盟之后,这个曾经被淹没在血海泪滔中的精神信仰派别,很快便沦落为思想的暴君。绝对一神论获得专制权力的附丽之后,便开始对思想异端的宗教审判;古希腊智慧的精神多样化的自由之魂和文化之美,湮灭于中世纪的千年黑暗,那是只被火刑柱上燃烧的思想异端者照亮的黑暗。试图消灭异教徒而发起的十字军东征,为大规模屠戮生命,找到了‘圣战’的道德理由。”
“命运以中世纪千年黑暗为鐡砧,以思想异端者燃烧的身体为火,锻造出西方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它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一种自诩绝对真理的精神信仰与专制权力形成同一个政治强权,这个政治强权把对人的控制,由社会领域推进到心灵的范畴——心灵被绝对真理的铁链束缚,人就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意义上变成强权的奴隶。”
“中世纪黑暗的太阳终于在古希腊自由文化传统的复兴中陨落。‘文艺复兴’运动是一次心灵的大起义。人的理性取代上帝的神性成为精神的权威,属于古希腊智慧的全部文化之美,以更丰饶魅力重返时代价值之巅。古老的法治和正义的理念,演进为民主宪政;精神多样化原则为思想自由奠基;‘人是万物尺度’的生命哲学箴言,盛开为人权意识之花。更重要的是,古希腊智慧对自然逻各斯的崇尚,升华为近现代的科学理性崇尚。从科学理性中新星系爆发般涌现出的物性能量,不仅使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法治、人权文化传统取得对西方中世纪极权文化传统的历史性胜利,而且赋与西方文化迅速击败东方文化,并主宰人类命运的机遇。”
“由于过分沉迷于心灵和道德,因而忽略了对自然逻辑和理性的关注,东方文化在一个历史时期中丧失通过科学理性的运用,获得强大物质能量的可能性,因而也就丧失同西方文化竞争的现实物性力量。近现代东方文化历史性失败的哲学原因,概源于此。当然,民主和法治的理念具有的社会正义的魅力,也为西方文化取胜东方文化作出政治道德的合理性诠释。”
“或许由于蔚蓝色的古希腊智慧本就有天空和大海般的精神包容性,以复兴古希腊文化而获得自由的人们,并没有对基督教的中世纪罪恶进行末日审判。相反,在基督教放弃神权政治,回归精神领域之后,西方宽恕了一个忏悔的上帝,并继续视基督教为一种文化传统和终极心灵安慰的来源。”
“基督教的上帝没有被判处死刑,尽管中世纪千年黑暗的罪恶,远超过萨达姆的罪恶。同时,中世纪的极权政治崩溃了,可是极权主义文化却仍然如幽灵般隐入虚无而又真实的时间,等待以新的生命形式复活的机会。极权主义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原因在于,它是人类贪欲的最具极致性的表述方式。商人试图通过金钱拥有世界和美女;专制者和政客通过追求权力实现对世界和美色的贪欲。古犹太智慧则创制出一种最彻底的获得世界所有权的方式:利用精神信仰和铁血强权的同盟——精神信仰为铁血强权作道德合理性辩护,铁血强权迫使历史接受精神信仰的绝对真理的地位——控制人类的心灵;控制了人的心灵,也就根本上控制了人,这个财富和美色之源。古犹太智慧比万年历史中的所有商人更精明,所有政客更阴险,他是从金钱和权力两个角度表述人类贪欲的商人和政客之王;对于人性黑暗的洞察使他确信,极权主义的幽灵永远能够在人类的贪欲中找到栖息之所和复活的希望。”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至少有又两次现实政治的复活,一次是纳粹主义运动,一次是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希特勒以屠杀犹太人为天职,而马克思身体里流淌着犹太人的血,但是这都不重要,因为,以古犹太宗教智慧为源头的极权主义文化,具有超越种族的诱惑力。纳粹主义的种族优越感制约了它荼毒人类的时间和空间。声称要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运动却成为人类的百年血祭,至今仍然向历史要求对人类命运的主宰权。”
“众多西方文人和政客都愿意把苏联共产帝国的冰消雪融视为冷战的结束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死亡。然而,这个结论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眼界中呈现的荒谬。真相是,共产主义所建立的东方巴士底狱,中共极权,仍然横亘在欧亚大陆东部的万里山河之间;现在看来,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表述的西方极权文化传统,很可能要通过中共暴政最经典地实现它的政治意志。”
“中国的伪自由知识分子和西方浅薄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即论证当代中国的专制是中国数千年皇权文化的结果。他们可能很难明白,他们实际在论证自己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蒙昧和中国现状的无知。二十世纪中叶中共建政之日,就是中国在文化精神的意义上亡国之时。中共对神州六十馀年的统治,就是用铁血强权摧残中国文化精神,使中国沦为德国犹太人马克思的政治和精神殖民地的过程。中共为确立马克思主义绝对真理的地位,对难以计数的坚守精神自由的中国人屠杀、监禁和流放。那些自由的灵魂消失殆尽,他们死去了,他们凋落了,他们被摧残了。随这些自由的灵魂一起消失的,乃是曾辉煌万年的中国文化精神。”
“中共专制者长著中国人的脸,他们的灵魂则与中国无关;他们不是中华文化的血脉传承者,而是马克思思想的遗嘱执行人;中国人实际处于精神亡国奴的地位。中共极权从政治风格到理论基础,都源自西方极权文化,那是与中国皇权传统有重大精神区别的另一种政治存在。在中共专制铁幕之下,中国文化精神早已变成废墟万里,中国的皇权文化只是中国文化精神废墟间随风飘零的残花枯叶,完全没有影响现实政治的可能性。”
“越过千年虚化的时间,以青铜色的落日为镜,我看到落日之镜内映出的中世纪基督教神权政治——那西方极权政治的最初形象,同当代中共极权如两副骷髅般相像。它们都用铁血强权确立并维护唯一的绝对真理,只不过神权政治的绝对真理叫作“圣经”,中共的绝对真理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都设立人类最美好理想境界作为诱惑,只是一个理想用‘天堂’来表述,一个理想则是地平线之外的共产主义;它们都要求对人的精神的绝对控制,而且都通过严酷的思想审判来实现它们的要求,只是神权政治更喜欢欣赏思想异端者在火刑柱上燃烧,中共则更沉迷于对自由思想者的长久的精神折磨;它们都用神圣的理想主义制造仇恨的道德理由,并以道德理由的名义纵情发泄凶狠的兽性,残害生命,不同之处只在于,神权政治的理想主义内容是在全世界实现基督教的大爱,其仇恨的锋芒指向异教徒,而发泄兽性的方式则是十字军东征,中共极权的理想主义之旗上书写的,是‘解放全人类’,仇恨的对象是原来的阶级敌人和现在的敌对势力,发泄兽性的方式则是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政治迫害;它们都设置一个直接同绝对真理对话的精神和政治特权阶层,作为极权的中坚,只是一个称为教士,一个称为共产党员;它们都把人类的命运置于绝对的宿命之中,不给人的自由意志留下任何余地,不同的只是神权政治的宿命论以上帝的意志为归依,中共极权的宿命论的根据则是物性的必然规律。”
“尽管中共极权与中世纪基督教神权政治,相像得如同两只苍蝇一样令人厌倦,却也有不同之处。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哲学基础属于精神领域,而中共的哲学基础则发端于古希腊智慧的唯物主义和诡辩论。不过,不同之中又显示出同一种权衡,就像远古的湖和今日的湖映出的是同一轮月亮——极权政治是一个狡猾的幽灵,它懂得按照不同情况,为自己选择最具时代合理性的哲学:在宗教情怀被奉为绝对精神的中世纪,它选择了宗教哲学;在科学理性获得近乎绝对精神权威的近现代,它选择了唯物主义哲学,因为,唯物主义距离以客体自然逻辑为前提的科学理性,比宗教情怀更近。”
“然而,正由于这个原因,中共极权便表述西方极权文化传统的最堕落、最凶残的形式。中世纪极权虽然吹灭了精神自由之灯,可是,它的宗教哲学的基础毕竟趋向心灵。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基督教神权政治还属于人的本质意境,即精神的范畴。唯物主义则把生命归结为物性——活着是一堆蠕动的物欲,死去是一块在腐烂中消失的肉。对人的本质怀有如此卑俗阴郁的观念,怎么可能尊重生命。而西方诡辩论衍生出的辩证思维,只能使唯物主义更诡诈,却没有能力使它接近属于心灵的真理。正由于包括中共极权在内的所有共产极权政权,都有一颗冰冷的物性的心,共产主义运动才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对生命的蔑视和摧残生命时的残酷性。中共极权成为万年历史中冷酷至极的专制动物,成为以受难者的血海为美酒的恶魔,其哲学原因就在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强权的结合。一个中共政治警察在审讯中,一根接一根折断藏人思想犯的手指;听到骨头清脆的断裂声,政治警察竟会露出享受的微笑。那位藏人思想犯从此厌恶并恐惧人类的笑,同时陷入深深的困惑:‘为什么我的指骨断裂的声音能让他如此喜悦?’”
“十五亿中国人的精神被囚禁在西方极权文化传统建立的现代东方巴士底狱内,并正在异化为否定人类自由的力量,所以,东方需要自由的拯救。而真正的危机则在于,自由本身也需要拯救。数百年前,自由理念击碎中世纪铁铸的千年黑暗,把人类历史推进到一个伟大的自由时代。然而,自由理念似乎已经在过去的时间中耗尽了精神能量,再也没有能力为当代人类提供理想主义的召唤——西方的民主法治原则仍然是社会正义的基石,而自由理念却已经衰朽了,因此西方需要拯救自由。”
“‘文艺复兴’以人的理性的名义,把神权逐下精神的王座;人权由此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权威,并构成近现代自由理念的价值基石。尽管人权意识的崛起是人类走出神权政治铁幕的精神动力,但是,人权戴上精神的王冠,却意味着另一次哲学危机的起点。”
“人是需要拯救的存在。因为,人并非纯然的善,而是善恶并存的二元结构;人的生命意味着善与恶进行百年决战的战场。物性本能和心灵共同表述人的生命。物性本能为人在现象世界中的存在提供生命形式和物性基础;心灵则使人获得万物之上的精神的命运。物性本能以个体的物性存在为真理,它为生命注入沸腾的物欲和自私的贪欲,从而形成人性之恶的源泉;心灵以美丽、高贵、道德性的存在为真理,否则宁肯不存在,因此,心灵是人类善的根据。人的命运的本质就在于心灵对物性本能的救赎,人也由于善恶的二元性不能成为绝对者。近现代人权至上意识或许源自一句古希腊哲学箴言:‘人是万物的尺度’。然而,古老的箴言却没有说明人应当以什么来尺度万物;有资格作万物尺度的唯有心灵,而不是生命的物性本能。”
“人类文明史过程中,智者和圣徒所从事的最重要的道德事业,便是用心灵的力量,约束或者升华物性本能分泌出的物欲和贪欲;在智者和圣徒的视野间,物性本能意味着万恶之源。近现代人权至上的理念却使心灵和物性本能同时获得自由的权利。这种看似平衡的状态实质上意味着人性的失衡。因为,心灵,以及属于心灵的美、高贵和道德是艰难的,是一条向上的路;物性本能,以及属于物性本能的物欲和自私的贪欲,是向下的堕落之路——心灵和善意永远比物欲和罪恶更艰难。物性本能一旦获得了与心灵同等的自由权利,心灵的历史性失败和生命物性本能的盛大凯旋就都不可避免。”
“现在,一个诅咒英雄、蔑视道德、理想主义凋残的时代,正证明心灵的失败,而疯狂追求物性享乐的生活方式则宣示物性本能对生命意义的征服。人已经异化为心灵之外的存在——一堆在痛苦而狂热的蠕动中渴望幸福感的物欲。但是,现代人离幸福只会越来越远,因为,他们在从不懂幸福的本能中索取幸福,而幸福只属于心灵;心灵之灯熄灭了,幸福感就隐入万古长夜。坐在豪华的宝马车中为追逐财富而焦灼的商人,没有可能比古代骑在瘦驴背上追寻诗意的苦吟诗人幸福。”
“心灵与自由一起在物欲中腐烂,自由又与道德一起死于自私的贪欲。生命的物性本能以人权的名义成为至上者,属于物性本能的私欲便主宰生命的意义。于是,利他主义的道德被时代放逐,社会共和精神如枯叶飘零,私利至上意念获得人性真理的权威。如果说生命的物欲化表述人以自由的名义对心灵的背叛,那麽生命的私利至上化则表述人以自由的名义对道德的背叛。背叛心灵和道德的自由,不仅没有拯救东方的精神能力,而且她本身就需要拯救。”
“二零零八年的金融危机不过是物欲化和私欲化的现代生活方式溃烂的一个伤口。各国的政客和经济学家试图从技术层次上解决危机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成功。从现代生活方式中涌现的经济危机本质上是哲学的。人类中的大多数都生存在形而下的范畴中,永远不会进入形而上的哲学意境,不过,从整体审视,人类的命运本质上属于哲学。所以,任何重大的时代危机,最终都归结为哲学的危机。当代精神危机的严峻之处,正在于哲学的贫困。东方处于卑俗的唯物主义哲学专制之下,西方人性的物欲化和私利至上趋势,使种种浅薄的实用主义哲学成为学术的时尚——哲学贫困到不能为人类提供走出精神危机的生命意义和理想主义的程度。”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同美国等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为主体的国家的冲突,被描绘为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另一种表现。但是,这种描绘也只具有表象的正确性。现在,很少有人愿意涉及一个事实,即伊斯兰教的上帝是唯一真神的信念,以及对异教徒的仇恨和用圣战消灭异教徒的观念,同属于基督教的真理一样,最初都发端于古犹太智慧;犹太教的神、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兰教的安拉,在唯一创世之神和唯一绝对真理的信念上,相似得犹如三滴从同一颗心中渗出的血。西方人不愿正视这个事实或许基于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厌恶;伊斯兰学者对此讳莫如深或许出于民族和宗教的自尊。但是,无论厌恶之情还是自尊,一旦成为表达真相的障碍,便不再值得重视。”
“把伊斯兰原教旨派别的恐怖主义视为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结果,乃是对东方文化的污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同美国的矛盾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千年恩怨的现代余韵,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超过百个世纪的仇恨,则是古犹太智慧的宗教情怀之子,因为,唯一真神的信念不允许两个上帝同时存在。同样源自古犹太智慧的伊斯兰教却以当代的犹太之国以色列为死敌,这是历史的宿命导演的悲剧。而伊斯兰原教旨派别和基督教之间的仇恨已经过分古老,古老得宛似早该被埋葬的干尸。”
“当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谴责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时候,他们应该意识到,通过圣战消灭异教徒和以屠杀异教徒表达宗教忠诚的信念,同绝对一神论之间具有难以割断的联系。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正充分展现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原始智慧的丑陋与罪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竟然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包括无辜的妇女与儿童,实施恐怖主义杀戮,这使得屠杀者沦为政治无赖;自杀式攻击者并不是在证明勇敢与荣耀,而是表述蒙昧者的疯狂。当塔利班炸毁巴米扬大佛的那一刻,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杀死的,不是佛的精神,而是伊斯兰的安拉。”
“伊斯兰宗教恐怖主义所象征的时代精神危机,实际是东方需要自由的拯救的另类表现。如果说中国需要从西方极权文化的政治制度遗产中得到拯救,伊斯兰恐怖主义则需要从西方极权文化的原始意识的遗嘱中,即绝对一神论中得到拯救。意识的拯救需要心灵的力量,然而,现在看来,美军的反恐行动缺少这种心灵的力量,伊斯兰教则依旧徘徊在历史的阴影中,还没有领悟到自我拯救的必要性。因此,伊斯兰宗教恐怖主义将继续作为当代精神危机的象征之一存在下去。”
“中共暴政通过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毁灭性开发,以及对数亿农民工三十馀年奴工般的劳动价值的剥夺,获得巨大的经济能量,而经济能量又转化共产极权主义运动再次崛起的信心。中共暴政已经成为当代精神危机的政治主题之一——中共极权的全球扩张预言着人类的政治大劫难。一百五十馀年前,中国还是被西方文化摧毁的东方文化的残破象征,当代中国竟又以西方极权文化传统继承者的资格,威胁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文化的政治存在;似乎曾经只属于欧洲的中世纪千年黑暗,又要覆蓋从东方到西方的整个人类命运。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通过怎样的逻辑形成的?”
“人类万年历史间,没有哪个时期哪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如同中国近现代史的文人这样,通过恶毒诅咒民族的文化精神来显示才华。民族的历史性失败当然有文化的原因。审视中国近代史的失败可以发现两个基本文化原因:在政治领域,以家族血缘为根据的皇权政治,无法同民主法治所表述的社会正义的时代进步抗衡;在现实力量的领域,从传统上对自然理性探索的忽视,到近代科学理性的缺失,使中国难以找到同西方竞争的物性能量的依托。但是,中国的文人却把中国近代失败的原因从整体上归罪于中国文化精神。他们背叛文化的祖国,侮辱文化的祖先,并选择作精神乞丐,向西方乞讨真理。”
“人的历史本质上是意志史;文化是意志的主要表现形式。民族的存在首先意味着独特的文化命运;背弃民族文化精神,就是背弃民族的命运和历史的传承,而背弃历史命运者,不可能拥有光荣的现实和壮丽的未来。历史命运的转变从来都不是推开一扇通向全新世界的门,而只有在历史的长夜中艰难跋涉,才能迎来命运的晨光。一个民族,尤其是作为重大文化历史象征的民族,也不能通过放弃自己的文化精神,而变成其它民族文化的表述——民族文化之魂是在同命运搏斗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放弃文化之魂的民族,必定失魂落魄,沦为卑微的行尸走肉。一个民族放弃了传统文化精神,就丧失了一切,就只配为别人的历史作可有可无的琐碎的注解。对于任何民族,传统文化精神都意味着存在的宿命。为追随时代进步的足迹,只能不断用创造性思维为这个宿命注入盎然生机,而不能也无法斩断她,就像不可能用刀锋斩断流水一样;如果一定要斩断文化的宿命,这个民族的命运也就如同无源之水,势将在历史的荒漠中干涸。”
“高贵者创造属于自己的命运,卑贱者靠乞讨而生存。向西方乞讨真理的中国文人不可能得到历史的尊敬。定然是历史在惩罚真理乞讨者,中国文人最后为中国乞讨到的,竟是西方文化最坏的部分——西方极权文化的现代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由此文化亡国,沦为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精神殖民地。中国的文化之魂一次又一次被淹没在政治迫害的血海中;中共暴政实质上是西方极权文化的政治代理人,中国人则沦为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和精神上的亡国奴。中共所炫燿的强大都不是中国的荣耀,而是属于西方极权文化的骄傲和中国的文化亡国的耻辱。”
“从以西方极权文化传统为魂的中共御用文人,到自诩西方自由主义继承者的中国文人,这两个似乎应当相互否定的群体,屁股上却都被命运烙上了同一个印痕,即毫无二致地恶毒诅咒中国文化精神,并痴迷于作真理的乞丐。中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西方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有的只是伪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应当称他们为伪类,因为他们的人格和灵魂都离自由主义很远。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哲学的理想主义,她坚信个性是生命价值的根据,是生命意义的基石,是生命自由的前提。然而,在中国文人的模仿者那里,自由主义的个性哲学却被理解为私利至上的原则。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一个伪类族群——伪自由主义文人。他们通过比猴子还糟糕的模仿,使自由主义蒙受侮辱。同时,中国的伪自由主义文人也从一个琐碎至极的角度显示出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的危机。因为,自由的概念在伪类的心中被歪曲地折射成对高贵人格的否定。”
“伪自由主义文人把本能视为生命价值的图腾,确认私利至上意识是自然的真理。他们仇恨英雄,因为英雄人格蕴涵的以天下正义为己任的侠义精神,使他们显得琐碎而渺小;他们嘲笑道德理想主意,因为,道德理想主义利益苍生的高贵的利他精神,映衬出他们小动物的本能丑陋。伪自由主义文人以自由的名义,使自己成为私利至上、私欲如炽的道德和理想之外的存在;那是一种类似于老鼠和苍蝇的本能存在。自由主义关于个性高贵的理念,竟在中国孕育出只能听懂私欲召唤的鼠辈和蝇群,也可谓思想史的一个悲剧。”
“世俗的伪自由主义文人庸俗得令人作呕,自称皈依基督教的伪自由主义文人则‘神圣’得令人厌恶。中国的伪类文人一旦获得基督徒的名义,便立刻在中国人之前显示出‘有信仰’的优越感,就像破落户突然捡到万两黄金一样神气活现。他们完全不理解,用信仰的理由蔑视人,比用金钱的理由蔑视人更低贱。因为,那是属于精神领域的低贱。”
“基督徒经过对中世纪神权政治罪恶的忏悔,已经懂得不再向信仰和精神多样化的世界提出挑战。但是,中国的伪基督徒们却沉醉于宣称要把神州变成上帝之州。中国伪基督徒让中国基督教化的野心,告诉世界下述事实:中国的伪类还活在中世纪的时间废墟中,他们还在遵循一种古老得早已朽败的信念,即用唯一并绝对的神控制所有人的心灵;他们完全不考虑如果中国基督教化,其它宗教或者生命哲学信仰在中国的命运,他们野蛮到完全不懂宗教宽容精神的程度;他们的意志犹如饱含宗教歧视的种子,正埋入中国的现实,并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清晨或者黄昏,怒放为血红的宗教仇恨和宗教战争的花海。”
“中国伪类的宗教野心在论证他们是精神自由的否定者,是以控制人的心灵为终极目的的西方极权文化的又一种复活形式。他们与中共极权的不同只在于,一个用世俗的形式表达极权意志,一个用宗教形式表达极权愿望。”
“用唯一的创世之神的名义确定绝对真理者,必定要欺骗世界。这或许是因为唯一的创世之神和绝对真理本身就意味着谎言。中国的伪基督徒经常重复一个经典谎言:应当把神州变成上帝之州的政治理由在于,基督教文化是民主的精神之源。这个谎言根本违背历史常识。正是基督教的罗马帝国国教化,彻底摧残了古希腊的民主法治学说,使欧洲陷入中世纪神权政治的专制黑暗——基督教曾经是屠戮民主法治意识的暴君,而不是民主的守护神。在‘文艺复兴’的精神解放运动中,基督教神权政治的凋残和近现代民主宪政的盛开,论述了基督教和民主政治相悖的历史命运逻辑。”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从中共御用文人到伪自由主义者,由于背叛文化的祖国和精神的故乡而被命运和真理所抛弃。打开他们干枯的灵魂,历史能看到的只是猥琐的欲望、知识的碎片、低俗的人格、炽烈的虚荣、虚假的热情和冷如蛇血的理性。人构成历史和文化的焦点,任何意义上的社会危机最终都通过人格危机呈现出来。当代的危机的极致,就在于中国文人所表述的人格堕落。那是西方极权文化传统用中国人的生命制造的人格奴性化、谎言化和物欲化的标本。中国文人人格破败的现状表述一个溃烂在时代之巅的真理:背叛了精神和文化的家园,知识分子的灵魂就是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狗。”
“在东方需要自由来拯救,而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的时代危机背景下,藏人走上民族的流亡之路。千万中国文人都把从各种角度诅咒文化的祖国当作时尚,藏人却为民族文化精神的生存而在刀锋般的命运之路上行进;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沉迷于物欲,藏人却以承受浴血的民族苦难证明对心灵的忠诚;世界各国的无数政客、商人、文人都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而视极权中国为经济朝圣之地,藏人却离开中国,并向中共强权索还精神自由——藏人的追求同一个堕落时代的丑陋逻辑完全相悖,藏人的流亡之路又怎能不艰难。但是,为了不死于物欲,为了活在心灵中,藏人必须承受艰难的命运;为人类得到救赎而承受时代的艰难,似乎是藏人的高贵天职… … 。”
金圣悲的思想消逝在暮色中。大地已经被坚硬如铁的深黑的色泽覆蓋,苍天却呈现为暗红色,像要渗出无尽的血泪。形似雪白日球遗骸的岗仁波钦此刻金霞辉煌,仿佛即将复活的古老太阳的魂魄。
“用心灵的苦难和染红苍天的血泪为一个堕落的时代献祭——难道这就是我追寻的藏人之魂吗!”金圣悲的一缕思绪好像被岗仁波钦峰体上流荡的金焰点燃了,然而,瞬间之后,哲人又陷入辽远的迷茫之中,“不,那不是藏人之魂,而只是藏人的命运… … 作高贵的心灵之祭。”
岗仁波钦峰旁现出一片铁黑色的晚霞;晚霞的形态酷似狂醉的激情。金圣悲平生第一次看到晚霞深黑如铁。他不禁沉迷于坚硬、深黑和霞的灿烂神韵凝结在一起的意境。他风中的红焰之心也为那种美而醉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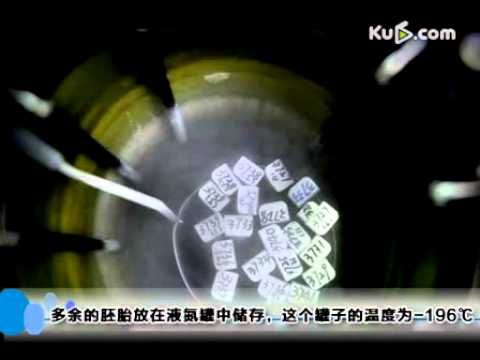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