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官网
配图(网络图片)
【鉴于自焚藏人已逾百人,现将袁红冰先生所著《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在网络刊载,以表达对自焚藏人的声援与敬意。 ——《自由圣火》编辑组】
第一章 当代英雄史诗
——藏人艰难并高贵在不相信英雄的时代
时间本无意义,是人的意志赋与时间意义,就像命运给了人灵魂。英雄史诗则是生命意义的华彩篇章。”
“当代,心灵腐烂于物性贪欲,精神之光黯淡;物性实用主义哲学成为生命意义的主题,理想主义如秋风中的黄叶飘零——这是一个背叛美与高贵,诅咒诗与英雄,并只懂得表述庸俗的时代。或许命运也厌烦了那令白玉之骨和铁石之心都生出斑斑霉迹的庸俗,从而引导一个高原族群,在这个不相信英雄的时代,用血和泪书写英雄史诗。”
“人类万年历史中发生过许多次民族大迁徙——为生存,为追逐丰美的水草或者财富,为逃离贫穷、奴役或者战乱而迁徙。唯有藏人,是为了心灵的信仰和民族文化的独特之美不被铁血强权灭绝,才踏上悲怆的流亡之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达赖喇嘛尊者,引领八万藏人,翻越万里云海之上的喜马拉雅冰峰雪岭,拉开当代藏民族流亡与迁徙命运的序幕:流亡,是为了信仰的自由;迁徙,是相信终有一日,能怀着圣洁的信仰,重返祖先的灵魂欢歌或者悲啸的家园。”
“藏人的流亡与迁徙,已成当代的英雄史诗;这首藏人的命运吟诵的英雄史诗,越过半个世纪,依然回荡在历史中。藏人的流亡和迁徙,是通向苍天的命运之路。连太阳都在物性贪欲中腐烂的时刻,由藏人的白骨与血泪铺成的命运之路,正坚守精神的启示;达赖喇嘛尊者在珠穆朗玛峰巅,那尘世的极致之处,为人类不死于物性的庸俗,点亮一盏心灵的金灯,这或许是人类得到精神救赎的希望。”
“是的,藏人已经证明,并继续证明自己属于英雄史诗的族群… … 。”
金圣悲在一个仅可容身的高崖岩洞内思索当代藏人的英雄史诗。从他端坐沉思之处,可以俯瞰下面漫长的雪谷。流亡的藏人大多都要经过这个雪谷。半个世纪以来,藏人的流亡从没有停止,就像高原上那永远不停的风——每一个流亡的藏人,都是一缕染血的风。金圣悲所处的浅浅的岩洞,最初是鹰的栖息之所,后来被一位苦修者占据。整整四十多年,苦修者在这个岩洞中为翻越喜马拉雅的同胞祈祷,直到生命枯竭。牧民告诉金圣悲,因为神佛佑护,巡逻的大兵都看不到苦修者。哲人却相信,真实的原因在于,苦修者枯槁似铁的容颜同岩石的色泽极其相近,士兵从远处看来,会把苦修者当作一块黑石。
“数十万藏人艰难的足迹曾走过这个雪谷,可是,只须一场风雪,一个民族走向心灵的足迹便被抹去,就像时间能令历史虚化。”金圣悲在思想中感到了命运的冷酷。半个世纪来,藏人踏着虚幻的时间和深深的白雪,行进在流亡之路上。流亡者有像高原上的草木花石一样自然的普通牧人,也有尊贵的法王和袈裟似火的僧人;有高级知识分子、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只能听懂风的歌声、读懂苍天启示的文盲;有双眸如星的少年、花季的少女、刚毅的男子汉,也有衰朽的老人和朝霞般的儿童。社会背景和生理状态如此不同的人群,竟会走上同一条命运之路——这是奇迹,也是一个困惑。活着的流亡藏人的数目有“十余万”,但是,死在流亡路上的可能更多。
开始探寻藏之魂的最初历程中,金圣悲时常向藏人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流亡?”但是,他却很少能得到明确的回答。金圣悲曾以为,由于流亡凝结了太多悲苦和深情,以致于藏人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渐渐地,从藏人有些厌倦的注视中,金圣悲意识到他的问题是愚蠢的——有谁能回答浩荡的风为什么要涌过铁褐色的荒野?只有完全不理解藏人,才会提出那种问题,或者说理解了,就不会再那样提问。其实,只要向脸形如鹰如豹的僧人的眼睛注视片刻,就会理解藏民族为什么流亡——一个以心灵的信仰作为生命意义的民族,怎么能生活在崇拜物性的铁血强权之下。
不过,无论原来有多少不同,只要走上翻越鹰也难以飞越的喜马拉雅之路,就都会面对同样的艰难。那种艰难属于血泪和白骨;对于藏人,流亡首先是一次踏着死亡的锋刃理解生命的精神历程。金圣悲以干肉充饥,以白雪解渴,以烈酒御寒,已经在岩洞上端坐了一日一夜。他本想进入理解生死的哲学意境,但是,昨夜他却领略到惊心动魄的悲情。
高原的暗夜,蓝得发黑的天空令人恐惧。虽说哲人是超越恐惧的族类,金圣悲仰望夜空时,仍然感到了心的战栗。蓝得发黑的天空仿佛一个宿命的预言:人最终将归于永恒的死寂,像一片冰冷的灰烬。那一刻,金圣悲万念俱灰,百思齐灭,想让自己的心,那团风中的红焰,冻结在白雪中。然而,悽厉、高亢的呼啸骤然撕裂了哲人的绝望。那在深邃的夜空中飞旋回荡的呼啸像是雪山的悲歌,又像是大地深处传来的雄烈鬼魂的咆哮。震荡在呼啸中的悲情,炽烈得能烧红顽石,能点燃铁铸的绝望。金圣悲第一次感受到,大雪山原来也有生命,否则怎么会在暗夜中发出如此震撼人心的呼嗥。
“藏人流亡命运的主题之一,便是能烧红顽石、能点燃绝望的炽烈悲情!”金圣悲红焰的心感到了璀璨的痛苦,一幕幕藏人翻越雪山的景象从他的意识中涌现。
一位决意为西藏独立而作铁血之战的青年告诉金圣悲,他翻越雪山时,看到一个年轻的尼姑冻死在齐腰深的雪里,她的脸形很美,可脸色却现出狰狞的紫黑色——那种美和狰狞重叠的感觉几乎让他发疯。这位青年还看到一头冻死的牦牛,祂倚岩壁而立,背上的筐里,有一个冻死的婴儿。虽然只向婴儿看了一眼,但是在那之后的一路上,青年觉得每一个黑色的石块都像那个婴儿的头颅。
一位如同金灿灿的麦粒一样丰满的姑娘告诉金圣悲,翻越雪山时,她的一位女伴嘴和鼻腔中突然喷出一阵血雾,然后就冻死了。死前她竟然从怀里掏出一朵小黄花——那是临行前她从家乡的雪水河旁采撷的。“我也不知道她想让我帮她作什么:是帮她把花儿戴在头上,还是让花蘸上她的血,等将来我回家时,帮她把花也带回去… … 她喷出的血红艶艶的,比阳光下的白雪还晃眼。… … 我该帮她作什么?”当时,那位姑娘对金圣悲如是说,不过,她又像在问撩乱她黑发的风。
姑娘给金圣悲看了她虔诚保存的那朵高原之花。花像圣物似的放在一个小小的银盒内;失去生机的花现出憔悴的枯黄,只是花瓣间的几丝殷红仍然色泽明艶——那定然是死者血的遗迹。凝视干枯的花,金圣悲想道:“当西藏自由之后,这朵花会被带回她曾盛开的故土;当那一天到来时,苍天定会降下血雨,哀悼这朵花的命运。”
一位长著羚羊般善良眼睛的青年告诉金圣悲,他们二十八个人结伴流亡。穿越边境的山口之前,他们用塑料袋把身体包裹起来,然后盖上白雪,只露出呼吸和观察的小孔,度过漫长的白天,以躲避中共的巡逻队。太阳落山后,他们看到十几个刚接近山口的尼姑被中共巡逻士兵发现。士兵开枪射击。子弹划出蓝莹莹的光线,射进尼姑的身体:尼姑站着时,僧衣像火;倒下时,僧衣像一片血,仿佛白得发蓝的雪地流血了。为救助还没有被打死的尼姑,藏在雪下的二十八个藏人几乎同时站起来。士兵们在震惊中停止了射击,并冲上来用枪逼住藏人。士兵只有五个人,其中一个用步话机向上级报告,说他们逮住了“二十八个畜生”,请求派人前来支援。
“我知道汉人看不起藏人。但是,亲耳听他们把我们叫作畜生,心里就像被扎了一刀。我冲上去,抢那个大兵的枪——死也要让他把那句话收回去… …. 。”藏人青年如是对金圣悲说。
当时,二十八个流亡的藏人一拥而上,制服了五个士兵。士兵吓得像“快冻死的羊一样发抖”。藏人青年用枪口对准那个士兵的嘴,但终于没有开枪。“我们没有杀死大兵。只把枪带走了,怕他们用枪打我们。没有杀他们,不是不该杀——他们杀死好几个尼姑。可我们是要到达兰萨拉去见达赖喇嘛;我不能用染上人血的手给尊者献哈达。”——藏人青年这样结束了他的讲述。
一位住在中国境内的七十多岁的汉族老人,给金圣悲讲述了他平生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这位老人当时是中共军队的一名士兵。他所在的部队进藏“平叛”,即镇压那次藏民大起义。他和他的侦察班,还有两只军犬,追逐翻越雪山的藏人时,围住了一个康巴女人。
“这个康巴女人又高又壮,跟一颗大松树似的,脑袋比牦牛头还要大。她用藏刀搏杀起来,就像藏庙里喝醉酒的护法神。她一边搏杀,一边大笑,笑声把人的心都能震碎。我们班的八九个兄弟都被她砍倒。她受的伤也不轻,流出的血把她的藏袍渗透了——浸血的藏袍沉得连大风刮过都不会飘摆。可她就是不倒下,好像杀不死的神灵。… … 两只军犬狂咬她的小腿,腿上的骨头都露出来了。可她根本不理睬狗,还用左手举起酒壶喝了几口酒,然后一刀就把我的军帽劈掉。我的脸就露出来了——是我的这张娃娃脸救了我,我当年已经二十多岁,可从脸上看就像只有十四、五岁。康巴女人可能把我当成小孩子,犹豫了一下,没有劈第二刀。我抓住机会向她开了一枪,在她脖子上射开一个血洞。康巴女人倒下之前,还对我伸出左手的小指,露出瞧不起的神气。她死前的最后一个动作,竟然是用藏刀在她小腿露出的骨头上敲了一下。她为什么这样作——是要听刀和她的白骨撞击的声音吗?我一辈子都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老人衰朽的声音中渗出一片困惑,结束了他的讲述。不过,即便是困惑,也丧失了生气,像暗灰色的落叶,似乎他的心早已干枯。
一位消瘦如岩石的老妇人,用佛殿中酥油灯的金焰般宁静的语调,向金圣悲讲述了她孙女的情与死。她的孙女生长在雅鲁藏布江边,从小痴迷于遥望金霞覆蓋的雄伟的大雪山。十六岁时,偶尔看到一张大宝法王的像之后,她就发下誓愿,要作大宝法王眼睛里的红杏花。为实现誓愿,她由老妇人陪同,沿大宝法王流亡的路线,走向喜马拉雅群峰;她相信,只要她能同英俊壮丽的大宝法王逼近地作瞬间对视,她的容颜就会永远怒放在法王苍天般的眼睛里。然而,翻越雪山时,她一边的脸被严重冻伤。虽然到达了达兰萨拉,她却不能去见大宝法王,实现誓愿。因为,她已经不能再盛放如红杏花了——她一边的脸依旧容颜如花,另一边脸却肌肉干枯,犹如铁铸的骷髅。于是,在大宝法王驻锡的上密院外默祷一夜之后,她一个人重新走进蓝天之上的喜马拉雅雪山。她要化为一缕永不超生的刚烈的鬼魂,佑护那些翻越雪山的流亡者,直到藏人不必再踏上艰难的流亡之路。
“在这个真情枯竭,心灵荒凉的时代,情感丰饶、心灵繁富的藏人,意味着生命的奇迹。藏人遗落在流亡之路上的悲情或者炽烈,或者艶丽,或者优美,或者深沉,或者灿若金霞… … 半个多世纪累积的丰饶的悲情,乃是苍天都难以承受的心灵之重。如果生命的深远处没有英雄的风格,藏人不会比苍天更坚韧。是的,西藏高原本来就是属于英雄的国度。”金圣悲在思想中离开岩洞,再次开始漫游。他的思想,则踏着雪山的峰脊走上苍穹之巅,俯瞰西藏高原。
亚洲中部有一个万山汇聚的山结,帕米尔;铁黑色的帕米尔,是西藏高原的命运之结。几道形如远古的狂涛巨澜般的山脉,以帕米尔为起点,扇形展开,向东方奔腾而去:东南方是汹涌在印度次大陆上空的喜马拉雅峰海;中部依次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喀喇昆仑-唐古拉山脉和壮丽的昆仑山,东北部是横亘在古丝绸之路苍天上的阿尔金-祁连山。这几条伟大的山脉经过万里奔腾之后,在辽远的东部突然被横断山脉的深峡截断——西起帕米尔山结,南以喜马拉雅为界,北以祁连山为疆,东以横断山为限,这是上苍为西藏高原界定的自然疆域。达赖喇嘛心中的西藏高原恰好与上苍的界定一致。尽管中共强权用政治的铁手割裂了西藏高原,并指斥达赖喇嘛提出所谓“大西藏”的概念。但是,历史将证明,上苍的意志比任何政治意志都更接近永恒;自然的界定比强权政治的意志离人性的真理更近。
西藏高原是最伟大的山脉纵酒狂歌的王国。高原之上,铁黑色的山体托起银白色的群峰,绵延万里。其中格外陡峭的山峰,有的像远古英雄激情的残迹,有的如同从大地深处冲腾而起的银火焰,有的似涌向苍穹之巅的龙卷风;其中特别雄伟的山峰,或者像王者的壮丽陵墓,或者如大海的雪浪托起的勇士的战盔,或者似鹰王和万里长风居住的金殿。暮色苍茫或者晨光清新之际,万座冰峰仿佛激荡在云端之上的雪水河,那里正是紫色的落日和金色的朝阳沐浴净身的地方。
金圣悲每次漫游西藏,都会为同一个信念而沉醉:只有英雄的壮丽命运,才配在这片高原上展开,而藏人正是西藏高原的选民。这不仅是因为藏人的心脏比低地的人更大,更强悍,所以适于高原生存——金圣悲并不关注这个,关注生理特征是医学家的事;作为诗意如花的哲人,金圣悲之所以确信这片高原是上苍为藏人选定的家园,完全在于藏族男人的形象最适于表述英雄人格之美。
卫藏的男人像铁铸的鹰,消瘦,但又敏感而锐利,清秀的气质中蕴涵着勇猛的神韵。安多的男人,头颅硕大,如岩石雕成;神情端庄、安详、辽远,令人想起暴风雨之后的荒野;他们仿佛总在遥望的眼睛深处凝结着刚强的意志,即便天塌地陷、太阳破碎,那男儿的意志也不会崩溃。不过,安多男人虽然形容粗犷,但很多人却格外精心地修饰自己的胡须:上唇的胡须形如两枚修长的柳叶,下巴上的胡须则像西藏艺人画美女的毛笔的笔端。岩石一样的男人竟把自己的胡须变成艺术品,也是一种英雄的诗意吧。
喜马拉雅是万山之王,康巴铁汉则是美男子之冠——那是壮丽辉煌的雄性之美。康巴男人,身形魁梧雄烈,纵酒高歌似悬崖起舞,昂视阔步如风暴临空;青铜色的面容刻出英俊猛兽的威严,黑得炫目的浓发间缠绕着红绸,像燃烧的云霞,像英雄之血的火焰。康巴男人,鼻如陡峻的山脊,眉似舒展的鹰翅,眼像彩凤之目;他们的双唇,轮廓俊美,形态丰饶,色泽深红犹如总在深情地亲吻火焰。当他们启唇一笑时,白齿闪亮,那双仿佛要看到人心底里的眼睛深处,会猝然涌现出灿烂的善意——康巴铁汉的笑能感染顽石,能让少女的骷髅喜泪盈框。
“鼻塌眼浊、腿短腰长、身形猥琐、神色低俗的南中国汉人,竟然也会从人种的角度蔑视藏人,那真是一种荒谬:鼠辈什么时候也获得了嘲笑壮丽猛兽的勇气?”金圣悲长叹如风。他坚信,藏人的天职就在于书写英雄史诗;藏人之美就在于表述英雄史诗的遗嘱。
“崇尚英雄的情怀,构成高贵而伟大的族群的生命标志。没有崇尚英雄情怀的民族,只是历史地平线上转瞬即逝的烟尘,没有谁会注意那种琐碎的存在。命运只会在时间的墓碑上,为英雄的族群刻出铁石的花环,以志尊崇。”金圣悲追随浩荡的风,走进远古的历史;在时间的深处,他可以用自己那颗红焰之心,亲吻英雄的血——那像深红的晚霞漫过铁褐色大地的英雄之血。
在民族历史的少年时期,藏人就以铁血英雄的意志,征服了远古的死寂与荒凉,成为这片离苍天最近的高原之上的王者。以王权作为政治标志的历史中,图博成为雄踞于世界之巅的强大帝国。当时的西藏高原是辉煌的雷电、浩荡的风暴和雄烈激情的王国;藏人的战刀和铁骑时常如苍穹之巅的太阳中迸溅而出的野性,从九天之上飞降而下,直击低地的大唐帝国。藏刀上流光溢彩的铁血战志,迫使华贵的大唐皇室不得不向藏人之王献出美女,以求苟安。
华美绝伦的古中华文化是金圣悲精神的故乡。不过,中华文化史中也常有令金圣悲黯然神伤的篇章。其中耻辱至极的,莫过于在强敌前用女色换取苟安的传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女人,本就是男人的原始耻辱——那是必须用血雪洗的耻辱。为苟安而向强权献出自己的女人,则意味着血也洗不去的耻辱。那种男人只配用女人的内裤蒙面遮羞,渡过残生。然而,中国男人的无耻还不止于此。中国的历代政客和文人竟然把出卖女色以求苟安的鼠辈丑行,描绘成杰出的政治战略;女人的色相换来的和平也被说成汉人的民族荣耀和历史功绩。堕落至此,太阳如若有情,定然也会羞惭得自溺于太平洋中,不再升起。中共的御用文人则更把历史的耻辱演绎为现代的无耻:即便鬼神也难以想到,他们会用唐皇被迫出卖公主,即所谓“和亲”的史实,作为“西藏自古属于中国”的谎言的论据之一。
“真实地面对耻辱,还有重新走向荣耀的可能;用谎言来修饰耻辱,则意味着人格的腐烂… … 。”金圣悲直视中国男人的肮脏与腐烂,竟然开始厌恶相关的思想;他甚至想剜出被弄脏的双眼,用雪水河洗去眼睛上的污迹。
大约从佛教被奉为国教起,暴风雪停息了,藏人大海般动荡的灵魂宁静了;西藏高原渐渐不再以雷电点燃的历史表述英雄意志,而开始用佛的沉思追寻心灵。有的研究者为此而困惑,他们看不清动荡与宁静之间的命运逻辑。其实,只要超越形而下的琐碎繁杂,达到形而上的明澈,逻辑就会清晰地浮现出来:所有逻辑的起点都在于苍天赋与西藏高原的神韵。
雪线是生与死的界限。雪线以下的高原之美属于生命;雪线以上的那超越生命的美,属于虚无——西藏高原本就是属于诗和哲理的王国。英雄时代吟颂生命之诗,佛的时代进入哲理。佛最深远的意境中呈现出的,正是纯净而圣洁的虚无的哲理和悲悯天下苍生的心灵。
像一团团火焰般在铁锈色的荒野上漫游的绛红色僧衣,取代藏刀和野花,成为藏人美男子的象征——这个历史的转变,具有超出藏人命运的意义。雪域高原,地球之巅,由超越物欲的信仰来管理,或许是一种天启的宿命;这个宿命与人类的生存和心灵的救赎直接相关。
西藏高原的雪山和冰川构成东亚和中亚的万河之源。从雪域高原奔腾而下的条条河流,养育了神州大地的古中华文明、南亚次大陆的古印度文明和东南亚半岛的文明。近现代的个人私利至上哲理和纵欲生命观中涌现出的生活方式,已使人类生存的自然背景遭到严重摧残。如果西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由于追求物欲的生活方式而崩溃,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将蒙受毁灭性的灾难,那或许就意味着古老的末日预言的实现。
由佛学信仰,即物欲净化后的心灵,来主宰雪域高原的命运,不仅会使万河之源免遭疯狂物欲的荼毒,为人类保留一片净土,而且在物欲中腐烂的人类,也可能从全民信教的藏人忠实于心灵的生活方式中,得到精神救赎的启示——幸福不在物欲中;心灵的宁静才是幸福的源流。
然而,中共强权暴政却逼迫藏人走上流亡之路。这不仅是中国的罪恶,东方的罪恶,也是西方的罪恶。因为,中共强权政治理论之魂,马克思列宁主义,乃是源自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现代经典。中共铁血强权迫使中国接受唯物主义。中共,这个只相信物欲召唤的政治动物,已经通过所谓经济开发,开始毁灭西藏高原生态平衡的进程。同时,中共也在用屠杀和政治迫害,以及物欲诱惑,使藏人离开佛学信仰,并背叛心灵。佛学乃是雪域高原的文化之魂,如果魂被摧残了,万河之源也将变成毒气污水之乡,山崩地裂之野,就如同中国的万里河山正在因为人的贪欲而经受的可悲命运。
很久以来,一份规划在中共高层政客和御用文人中广泛传阅。规划名称叫作《大西线工程》,其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引导西藏流向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的重要水流改道,转向中国北部,解决华北和西北部分地区水源枯竭的危机。这个与自然逻辑相悖的疯狂规划一旦实施,必然引发地球循环系统失衡;可以预见,人类生态危机将成为规划实施的悲剧性表述。同时,为争夺水源而爆发世界战争将不可避免;人类会再次回到万年文明史之前的荒蛮的起点——道德、良知、理性等等所有这些文明的法则都失去作用之后,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定然成为万法之王。
《大西线工程》是一种疯狂的非理性。不幸的是,它很可能再次取代理性,主宰雪域高原,乃至人类和地球的命运。因为,所有极权者或者寡头集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战略决策的非理性和实施战略决策的高度理性。
两线作战是兵家大忌的非理性决策,但是,希特勒就以出乎所有战略家之意料的两线作战,将二次世界大战推向惨烈的极端;二次大战时,连日本军阀都根据理性分析得出结论:由于经济能量的差距,日本同美国开战将必败,然而,日军依然奇袭珍珠港,向理性发出铁血挑战;当年,几乎所有的美国军事专家都认为,装备低劣的中共军队不可能入韩作战,因为,那违背理性的权衡,可是,中共的实际行为却羞辱了美国军事专家的理性和智商。
与之同时,极权者战略决策的执行却又充满沉静到冷酷程度的理性。无论德国的闪电战、还是日军奇袭珍珠港的战术安排,或者彭德怀的大纵深穿插推进伏击的战法,其理性设计都精确得像瑞士的钟表。极权者战略执行过程中的绝对理性,正是其战略决策非理性的效能倍增器,它可以使非理性的战略决策迅速进入历史,并摧残人类的命运。
极权者都是精明的蠢货:精明在于政治权术和阴谋,在于应对现实危机的机巧;愚蠢则在于对自然精神的宏观蔑视,以及其对心灵的无知。中共极权者由于崇拜唯物主义而更是如此。所以,除了战略决策的非理性特点之外,中共当局也很可能在现实危机的逼迫下,实施《大西线工程》。以毁灭性开发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非理性发展,已经使中国北方生态系统进入崩溃程序,沙漠化的趋势与水资源的枯竭齐头并进;十年之内,中国将出现数亿生态难民。如果中共极权还能生存得足够长久,它就只能通过把雪域高原的水大规模引导向北方,解决直接威胁其专制政治生命的生态难民危机。对于中共极权,维护其政治存在是最高意志;它根本不在乎这种饮鸩止渴、割肉自啖式的作法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它的全部聪慧就在于用一个更严重的罪错,弥补原来的罪错。
事实上,中共早已经通过滥采矿藏和在河流上大量筑坝,拉开彻底毁坏西藏高原自然逻辑的序幕。直视高原未来的自然命运面临的困境,才能理解达赖喇嘛尊者关于把西藏建成世界和平区建议的慈悲之心。源自佛学的和平理念,既意味着对人类之间战争的否定,也意味着人对自然逻辑的尊重。只有一个在圣洁的佛学中沉思心灵的西藏,才能避免出现一个因物欲追求而疯狂的高原——如果世界之巅由于物欲的疯狂而失去理性,人类的历史定将在非理性中万劫不复。
“尊者已经把真理告诉世界,人类却缺乏理解并实现真理的能力。一旦佛光随最后一次落日的紫霞从雪域高原上消失,西藏将进入永恒的长夜,万座莹白的冰峰雪岭会由于物性贪欲的侵蚀,而变成枯黑的真理的墓碑… … 。”金圣悲的思想走上了断崖,他又一次悲哀地感到了真理的软弱,同时也感到了实现真理的责任和希望:“实现真理是为了得到心灵的安宁,而实现真理的希望也正在于心灵——藏人心灵的力量。是的,真理的希望在藏人的心灵间栖息,藏人同中共的全部冲突,都集注于对待心灵的态度。”
毛泽东曾经对达赖喇嘛说,佛教害了藏人。他的意思可能是,藏人强悍的铁血意志和野性锐利的生命风格,由于佛学而变得柔软,变成一种心灵的沉思,因而丧失政治和军事强者的历史地位。
然而,毛泽东是愚昧的——这个物性世界中的权术大师,蒙昧于心灵。人从自然逻辑中脱颖而出,获得独立于万物之上的意志的命运,获得以审美激情表述宇宙精神的权利,全在于人的本质是心灵的存在。蒙昧于心灵者离人的本质比有限离无限更远。毛泽东没有能力理解,进入佛的意境之后,藏人虽然失去了政治和军事的强大,却在更深沉的意义上变得强大,那是属于心灵的力量。
在半个多世纪中,中共暴政用滔天的血海、蔽日的军刀和十万铁牢,都不能灭绝藏人的信仰,不能阻绝藏人的流亡之路——这是藏人心灵强大的证明。不过,当人类整体都因为迷醉疯狂的物欲而丧失生命意义的灵性时,在一个背叛心灵之美的时代,藏人由于忠实于信仰而承受青铜色的苦难和冷酷的死亡,则是心灵强大的更经典的表述。
数十万踏上流亡之路的藏人,没有一个是基于追求物欲或者世俗利益,使他们从容承受命运艰难的原因,只在于心灵或者精神:法王流亡是为接近中共不准返回故乡的佛学上师;僧人流亡,是为撕裂极权铁幕,聆听真实的佛法;诗人流亡,是为自由的吟颂;像高原的风或者草木岩石一样自然的普通藏人,最具感动历史的魅力,他们只是为了能来到达赖喇嘛的身边而万里流亡——那种虔诚的宗教感情并非世俗意义上的个人崇拜,而是心灵对佛的精神的皈依。
政治奴隶无真情。实际处于中共暴政政治奴隶地位的中国人和伪自由知识分子在嘲笑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感情时,他们应当知道,诸如他们一类丧失了虔诚的情感能力的人,不过是一个个谎言化的生命;谎言没有资格嘲弄虔诚——如果他们不知道,那麽他们便比谎言更可悲,也更猥琐。
金圣悲访问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的学校时,遇到过一位小女孩。女孩来自雪域高原的拉卜楞寺,今年已经十多岁,读初中的课程。她的父母在她五岁时,托人把女孩带到达兰萨拉,目的是为让她学会藏文。女孩向金圣悲展示一篇她用藏文写的文章。那一行行藏字形态优美,宛似迎风翩翩起舞的思念。
女孩长得健康而饱满,犹如一枚多汁的野果;眼睛纯澈得像融化的高山之雪。尽管初识,她却把心中最关注的事讲给金圣悲听——女孩依然相信人这个概念。女孩讲,当年是一位小哥哥背她走到尼泊尔的;翻越雪山时,她的围巾被风刮走了,小哥哥把自己的帽子给她戴,耳朵因此被冻伤。女孩来到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之后,那位小哥哥一次也没有来看望过她。有人告诉她,小哥哥不来看望,是因为冻伤的耳朵后来掉了——他不愿让她看到自己没有耳朵的样子。
“我长大后,一定去找小哥哥。他在印度南方。”女孩说出一个誓言。
“到时你还能认出他吗?”金圣悲下意识地问。不过他立刻就后悔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作为一个哲人,为什么竟会关心如此形而下的问题,或许只是因为他太希望女孩长大后能找到那个“小哥哥”——人世间美情感的结果常是悲伤与哀愁,而他希望女孩成为少女后,眼睛里能闪耀起无尽的喜悦;他坚信,在女孩的心灵和眼睛里,没有耳朵的“小哥哥”都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男儿。
“这不用担心,我一定能认出他来。”女孩很快回答:“不过不是认出他的脸… … 我都忘了他的脸是什么样子,但我能认出他的背面——认出他的脖子和脑袋后面的头发。逃出来的时候,他每天背着我,有二十多天,整天我都看着他的脖子后面和头发。现在,我有时会记不住我自己在镜子里是什么样,可我忘不了他的脖子和头发… … 他的脖子后面中间有一个像小米那麽大的黑痣,头发上有两个旋。”
女孩眼睛里忽然泪影晶莹;金圣悲震惊地发现,女孩的泪影竟然呈现出青铜色。“女孩的眼泪应该像花露一样清香而流光溢彩。她的泪影为什么会是青铜色?那是多么坚硬而又哀伤的色彩呵… … 。”金圣悲在困惑中离开了女孩。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被什么感动——是女孩对“小哥哥”晨雾般迷茫而淡紫的纯情,还是女孩父母对藏文化的深情。像女孩这样从小就被父母送到达兰萨拉学藏文的男女儿童有许多。父母的心坚硬到怎样的程度,才会把孩子,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骨血,送上艰险莫测的万里流亡之路,送进暴风雪弥漫的命运之旅。而比他们的心更坚硬的,乃是一个族群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苦恋和对精神故乡的忠诚。
半个多世纪的迫害、酷刑、屠杀和诱惑,却不能改变藏人灵魂的风格。高原的酷寒能冻裂铁铸的心,可冻不裂藏人的信仰;藏人的心灵就是刻在牦牛头骨上的彩色经文,高原的风能吹裂顽石,可吹不裂洁白如雪山的牦牛头骨。当前,世界各国多如印度夏日之蝇的政客、商人、文人,服从世俗物质的诱惑,以种种猥琐的姿态,在中共极权前争宠献媚。在这精神艰难的时刻,藏人只为心灵的原因,而用胸膛与中共强权的屠刀抗争。这种“孤独”,正表达心灵的强大。
“心灵常常受到物欲的嘲笑,因为,历史总在物欲的诱惑下,进入庸俗、污秽、堕落的时代。这一切似乎在证明唯物主义的结论:人本质上是一堆灼热的物欲;物欲是主宰历史进程的王者。不过,在命运的关键之点上,心灵会以圣洁的信仰和激情,引领人类走向高贵与美。之所以如此,或许基于一个精神哲学的信念:人本质上是‘追求意义的动物’;意志的历史最终要听从心灵的召唤… … 。”
金圣悲在思想中漫步,他看到,藏人翻越喜马拉雅的白骨与红血之路,伸展向时代的精神之巅;藏人正在由于对心灵的忠诚而感动历史,当人类有一天从物欲的黑暗中仰视苍穹,寻找启明星时,会从藏人苦难的心灵史中看到精神的希望。中共暴政不会想到,它把藏人逼上流亡之路,而那条离开尘世中的祖国的路,既是重归心灵的故乡之路,也是走进人类历史中心的光荣之路。暴政在用浴血的苦难,为藏人编织值得供奉在太阳之巅的荣耀的花环。
金圣悲红焰的心在炽烈的疼痛中震颤,那是只有用关于英雄的思想才能抚慰的疼痛。于是,他在烈焰的疼痛中开始了思想:
“藏人的流亡是当代的英雄史诗。半个多世纪抗争的意志,既来自心灵信仰,也源于古老的英雄人格。藏人的历史从英雄时代进入佛的时代之后,英雄人格却并没有凋残,就如同银白的冰峰上,金色的霞影在每个日落时依然重现古老的灿烂。值此中国文人中自命自由主义者的小男女恶毒诅咒英雄的时刻,西藏高原仍然坚守对英雄的敬意。格萨尔王传奇,那随摇摇滚滚的风在铁褐色大地上四处漂泊的游吟诗人传唱的史诗,正是藏人生命风格的表述。游吟艺人相信格萨尔是佛学大师莲花生转世——这证明在藏人的灵魂中,诗与哲学凝成同一颗情感的露珠;英雄人格和慈悲的佛理共同托起格萨尔传奇,这人类英雄史诗之王。称格萨尔传奇为英雄史诗之王,并不是由于它的篇幅比所有的史诗漫长——再长也没有时间长;也不是由于它的诗意丰饶如海——世界上每一篇史诗都有独特的美色,而是因为所有民族的英雄史诗都早已成为历史废墟中的墓碑,成为文化考古的对象,而格萨尔传奇仍然活在藏人的灵魂深处,活在西藏高原荒凉而美的地平线上。英雄史诗因藏人的灵魂和雪域高原而不死。”
思想重归英雄人格的意境,使金圣悲生机盎然。他一直把英雄人格和美设定为他哲学的主题;此刻他发现,英雄人格和美也是藏人生命的主题。他曾欣赏过一幅西藏工笔画艺术风格画出的格萨尔王的形象。画面上,格萨尔王正纵马奔腾在彩云之端。他的坐骑是红得比火焰还艶丽的雄马,马的体形宛似飞奔的猛虎;格萨尔金盔银甲绿带,手执战旗,追逐雷电萦绕的太阳。整个色彩繁富的画面激荡著狂风怒涛般的动感,显示出属于雄性的壮丽与华贵,强悍与辉煌。就在看到那幅画的最初一刻,金圣悲感到,在审美激情的意义上,他同藏人之间似乎有某种古老的心灵默契。
鹰群的铁黑色长翼划伤了蓝天,被蓝天之血染成紫红的流云,萦绕在金圣悲身旁,引导他来到一座山峰旁。岩石的峰顶呈现出铅灰色,破裂的岩体极其陡峻,就像烈马狂奔前的瞬间机警耸起的耳朵。山峰中部岩洞外的陡坡上,是格萨尔王和他的十几位将领的墓。一条峰脊从右边围绕住墓群,如同陡峰的手臂护卫著英灵。
陵墓形如一座座白银铸成的战盔,墓群周围的岩壁渗出淡淡的枯红,像远古的血迹,那正是适于哀悼和沉思英雄的色泽。金圣悲背倚格萨尔王陵的墓基,盘膝端坐。他根本不在乎关于格萨尔是真实的存在,还只是传说中的人物的争论;对于他,知道格萨尔史诗的英雄人格是藏人灵魂的真实内涵就足够了。他坚信,墓群下埋葬的定然是雷电和狂风般的英雄男儿的遗体,而格萨尔王墓下埋葬的则是金色落日的骸骨。
从金圣悲端坐之处望去,对面的山坡上有几株杜鹃花树。此处的杜鹃花呈现为蓝白色,可是怒放的花形却风格繁富——淡雅的色调与繁富的花形构成一种醉人的美感,仿佛纯洁的藏族美少女对英雄的迷恋。
杜鹃花树随蓝色的风摇曳生姿,使金圣悲的思想飘摇在诗意之中,难于进入哲学意境。大野寂静,英雄格萨尔的陵墓向怒放的杜鹃花的永久凝眸中,似乎涌现出与彿学哲理一致的生命美的意境。金圣悲的眼睛格外明亮地闪烁了瞬间,而他的思想比眼睛更灿烂:“难道我已经找到了藏人之魂?在宁静至极的寂灭和满月般晶莹的虚无——那佛的精神背景上呈现出的英雄人格和招摇的杜鹃花的花枝,便是藏人灵魂的象征。明知终将归于寂灭,神形俱消,也要在短暂的生命中坚守心灵的信念;明知命运终将化为虚无,也要用英雄人格和花枝表述对瞬间的生命之美的崇敬与忠诚——这便是藏人的魂吗?”
不过,金圣悲的眼睛很快又变得苍茫了。他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找到藏人的魂。因为,他红焰的心依然没有熄灭;红焰中,梅朵依然在作妖娆而苦痛的焚身之舞。冥冥之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藏人的魂比你想的离自然更近。”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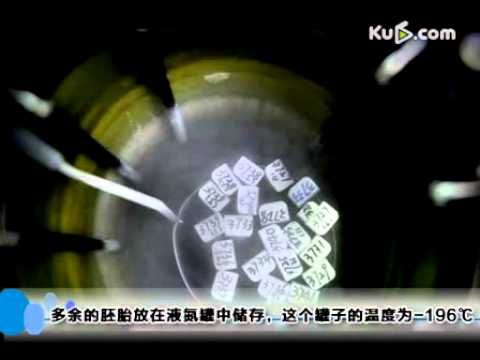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