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中官二代的紅衛兵(圖片來源:網路)
【看中國2017年12月13日訊】1965年,當北島邁進無數人夢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門時,才發現這裡並不是天堂。除了繁重的學業外,每天被騎進學校的高級進口自行車,飄蕩在耳邊的高層小道消息,以及每週末只有高幹子弟有資格參加的會議,都讓他感到莫名的自卑和壓抑。而在同時,所有人的衣著卻又都很統一和樸素,甚至樸素到了可疑的地步,顯得很「平等」。這讓北島感覺很不對勁:「顯然有什麼東西被刻意掩蓋了,正如處於潛伏期的傳染病,隨時會爆發出來。」
直到文革的某天,北島走進教室,忽然大吃一驚:高幹同學們已經搖身一變,披上了簇新的綠軍裝,甚至呢制的將校制服,腳蹬大皮靴,腰扎寬皮帶,手臂上的紅衛兵袖標紅得耀眼。紅色貴族們的這身華服,瞬間將自己與其他同學截然區分開來。這時北島才恍然大悟,之前自己的壓抑,原來就是來自這種隱而未發的優越感。
終於,它「卸去樸素優雅的偽裝,露出猙獰面貌。」
《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是18位親歷了文革的四中學生的回憶錄。由於書中大部分作者都屬於寒門子弟,所以文革前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是他們的共同記憶。比如在王祖鍔看來,當時階級路線被貫徹得越來越嚴格,無論是上學、參軍還是工作,都要看出身,家庭背景不好的人處處受限,根紅苗正的人則享有很多便利,「人與人的不平等到了如此地步,有些人還是不滿足。」趙京興則說得更大膽直白:「按照教科書和老師的講法,社會主義社會是個美好的社會,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事實並非如此。」
用不平等、壓迫等常與資本主義相聯繫的詞來描述社會主義社會,這乍看起來很令人驚訝。但正如卡爾.波普(Karl Popper)所說,即使在共產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後,馬克思預言的「無階級的社會」也不會出現,因為就在推翻舊政權的那一刻,「手握權力的人很快便會組成一個新的貴族或官僚階級,並成為這個新社會的新統治者。」他們會極力掩飾這一點,而最好方式莫過於保留並利用原有的革命意識形態,充分利用它,「一方面,使這些新統治者的權力合法化,並不斷得到加強;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精神鴉片’來麻痺無知的民眾。」
高幹子弟和寒門子弟之間的利益衝突,才是產生全國性紅衛兵運動的社會基礎,文革也是當時「社會矛盾的總爆發」。49年後,紅色貴族的權力則乘機無限膨脹。不知不覺間,人民內部已經形成了四個階級。四中學生就是當時社會結構的縮影:高幹子弟的地位最高,工農兵和普通幹部子弟次之,知識份子的後代再次。「黑五類」子女則早已淪為賤民,絕對進不了四中。
文革開始後,高幹、工農兵、知識份子二代都組成了各自的紅衛兵組織,分別稱為「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雖然這三派紅衛兵都使用相同的革命話語,一眼看上去似乎沒什麼區別,但只要從他們的具體行為和立場來分析,就能看出這三派紅衛兵其實有著各自明確且迥異的政治訴求。
「老兵派」又被稱為「第一代紅衛兵」,顧名思義,他們是率先投入文革浪潮的。由於能通過家庭在第一時間瞭解高層政治動向,他們可以先發制人。文革初期是「老兵派」的天下,他們提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著名口號,並由劉輝宣譜寫成《紅衛兵戰歌》,迅速傳遍大江南北。隨後的3個多月時間裏,全國圍繞著「血統論」和「出身論」爆發了激烈的爭論。雖然當時所有社會資源都已經向紅色貴族們傾斜,但他們還是不滿足,擔心「狗崽子們要翻天」。所以,他們要利用文革,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對於這個意圖,「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寒門子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們暫時敢怒而不敢言。
「老兵派」的行動緊鑼密鼓。6月初得到毛澤東有意廢除高考的內部消息後,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的十幾位高幹子弟立即起草了「廢除現行高考制度」倡議書。此倡議書由劉源提交給時任國家主席的父親劉少奇,並隨即見報。這份倡議書稱,高考制度「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制度的框框,不利於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來的教育方針。」但其實「老兵派」更隱秘的動機是借由廢除高考,徹底堵塞寒門子弟向上流動的渠道,建立某種「社會主義門閥制」,讓紅色貴族們世代掌權。
但是,風光了幾個月後,毛澤東在8月5號忽然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將矛頭直接指向劉少奇和整個官僚階層,並隨後解散工作組,卻使得「老兵派」的形勢急轉直下。我們至今無法確定,毛澤東的這一舉動,究竟是緣於對官僚階層的不滿,還是為了打擊政治異己,攫取更多個人權力。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此舉為之前被壓抑很久的「四三派」、「四四派」,即「第二代紅衛兵」的橫空出世掃清了障礙。尤其是8月18日受到毛澤東親自接見後,「四三派」、「四四派」紅衛兵更是強烈地感覺到,「毛主席」是支持他們的。他們因此陷入領袖崇拜的迷醉中無法自拔,並在隨後肆意「傾瀉我們無情的暴力」,直至掀翻天地。
「四三派」和「四四派」(寒門子弟)的政治訴求與「老兵派」(高幹子弟)針鋒相對。前者要求的是「打碎特權階層」,剝奪紅色貴族的權力,「實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遇羅克的《出身論》是「第二代紅衛兵」的政治綱領。在他們看來,劉少奇是支持「血統論」的,代表官僚階級的利益;而毛澤東則是支持「出身論」的,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所以,他們強烈要求打倒劉少奇。作為精神領袖,遇羅克始終對毛澤東抱著很複雜的感情。但是在「血統論」橫行太久的情況下,除了支持毛外,實在是沒有其他選擇。在遭逮捕並被處決前,遇羅克還將一封長信交給牟志京保管,「在今後情勢允許時,交給毛澤東」。
總體來說,在所有的紅衛兵派別中,「老兵派」是相對來說是最「理智」,破壞性也是最小的。暴力畢竟只是他們用來顯示自己「革命性」的手段而已,對於這個遲早會從父輩那裡繼承過來的江山,何必要將其打得千瘡百孔呢?「老兵派」希望的是文革不要持續太久,達到目的即可,見好就收。但「四三派」「四四派」中的很多人則純粹是為了發泄對社會的不滿而投身文革,是為暴力而暴力。在著名「紅八月」裡,他們走上街頭集體狂歡,一時血雨腥風。本著「凡是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的原則,「四三派」、「四四派」由一開始反對「老兵派」,反對官僚階級,進而發展到反對社會的一切秩序,無論它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
這種破壞一切社會秩序的狂熱被黑格爾(G.W.F. Hegel)稱為「否定的意志」,這種意志「只有在破壞某種東西的時候,才感覺到它自己的存在」。通過無止境的破壞,他們暫時獲得了一種空虛的自由。「這種意志以為自己是希求某種肯定的狀態,例如普遍的平等,但是事實上它並不希望這種狀態成為肯定的現實,因為這種現實會馬上帶來某種秩序。」他們擔心一旦文革結束,舊有的金字塔形等級制便會死灰復燃。他們渴望的「真正的社會平等」只能是幻想,因為「這觀念實現的只能是破壞性的怒濤」。
單從力量對比上看,寒門子弟人數遠遠勝過高幹子弟,所以前者能在短時間內扭轉局勢。但權力資源畢竟是有限的。奧爾森(Mancur Olson)就曾指出:「比起大集團來,小集團能夠更好地增進其共同利益。」文革初期的「老兵派」由於人數少,容易統一行動,所以局勢始終在可控制的範圍內;但「四四派」、「四三派」則由於人數眾多,在短暫的一致對外後,便無法統一行動,反而分裂為很多小派別,為爭權奪利而開始倒戈相向,武鬥浪潮隨之席捲全國。
發展到最後,紅衛兵運動脫離了追求「平等」的初衷,只剩下野蠻的權力鬥爭。有的人始終一往無前,最終碰得頭破血流,甚至肉體湮滅。有的則被現實的血腥和殘酷所深深震撼,開始閱讀各種書籍,並痛苦地思索這場運動的意義。毛澤東也意識到不能再這麼下去,於是便提倡上山下鄉,把紅衛兵分散到農村的「廣闊天地」中,藉此稀釋其破壞力。於是1968年,一批批的紅衛兵帶著困惑和失落,經火車站離開一片狼藉的北京城。他們完全沒意識到,遠方荒涼且貧瘠的農村將成為他們的煉獄。
在「四三派」、「四四派」紅衛兵看來,文革中的他們是「為爭取平等而鬥爭」,若非他們挺身而出,中國早就建立起嚴密的金字塔形等級制了。而在「老兵派」看來,他們在文革中始終代表著一股「穩定的理性的」力量。他們在「紅八月」局勢失控時組織「西糾」,通過一系列行動試圖阻止流血事件的蔓延。隨後更是成立了「聯動」,公開反對「中央文革」,甚至還要「打倒江青」,並「徹底批判毛主席的錯誤路線!」這難道不是有反文革的正面含義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兩方都能從自己的角度來為自己辯護,這是文革以後,很少會有紅衛兵進行主動反思的根本原因。
而在上山下鄉運動中紅衛兵(知青)所受的種種磨難和不公待遇,則使他們轉而認為自己才是文革中真正的受侮辱與損害的人,由於這苦難,之前犯下的罪惡似乎都可以一筆勾銷,「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身份也在不知不覺間被完全顛倒過來——這是永恆的規律:比起加害行為來,人類更容易記住的是受害體驗。
也許文革的唯一貢獻,就是讓大部分人看清楚: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不但不會帶來物質財富,甚至連其最引以為傲的「人人平等」,也不過是張空頭支票。有些問題似乎永遠難以解決:1968年「四三派」和「四四派」鬥得血肉橫飛時,一個已失勢的「老兵派」同學依然無比高傲。他極為自信地跟北島打賭「二十年後見高低」,並稱「你們有筆桿子,我們有槍桿子,看將來是誰的天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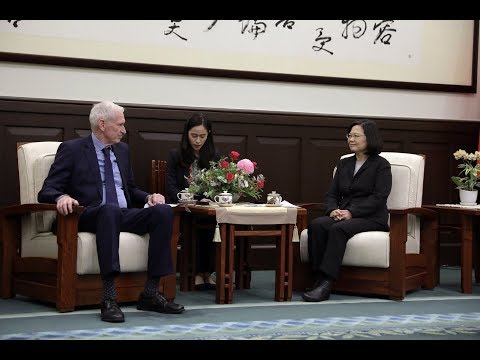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