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一百三十
见到母亲,临时改变了主意,暂不打算去她那里,先把急需办得几件事情赶快办完。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独自走出城来,向南磨村的方向踽踽前行。过去的路大都废弃,由东北向西南本来是斜路,农田基本建设后,都改成了垂直的路。但我还 是非常熟悉这儿的地形,小时候,和姥爷一起放牲口,走遍了这一带的每块地。在县城上初中那三年,礼拜天常去姥娘家,也都从这里经过。十七年前,当我戴着那 顶沉重的帽子回来时,走在这条路上,既怨恨又羞愧,真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觉得无法面对自己的亲人。十七年过去了,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再次踏上这条路时, 仍然高兴不起来,曾经给亲人们带来的痛苦,今生今世怕也难以弥补,虽然已经平反,头上的帽子和紧箍咒终于去掉了,但因着我,亲戚们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拖 累,那将是我最对不起他们的地方。
春天来临了,路旁的柳树、杨树争先恐后地发出新芽,有的已经变成黄绿色的小叶,微风吹过,发出柔和的轻微的响声。啊,久违了,田野、土地、小路、树木,这 儿那儿已经有人在耕种。十几年来,我像一只井底之蛙,活动在那么一小片地面中,眼前看到的除了阀门和砂子,就是黑乎乎的厂房和黑乎乎的路面,从来感觉不到 春天的气息,大自然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现在,终于自由了,重新徜徉在田野里,并不急着赶路,慢慢走着,沐浴着春日的阳光。过了农校,有一条小河,一九五 八年,在河上修了一座小型水库,从前每次路过这儿,都要流连很久。雁门关外,多得是白草黄沙,能有一汪清水,自然会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然而现在却没有 了,库底载满了杨树,间距很近,大约是为了卖树秧子。早年间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河,不仅干涸,甚至失去了河床,深沟几近填平。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保留一汪清 潭不是很好的吗?
走进村来,这时虽在耕地、播种,毕竟只用少数劳力,村里的街道上还有不少闲人,几个老年人认出我时,大家马上把我围拢起来问长问短。小时候,在姥娘家住了 三四年,上了年纪的人都认得我,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对我的归来,不约而同地表示祝贺,也有几个老年妇女感叹道:“唉,可惜他姥娘前几年走了,听说临咽气 时还不住地叫着他的名字哩,三老人最亲她这个外甥了”。听到这话,一股酸楚味涌上心头,强忍着快要掉出的泪水,应付着大家的问话,然后慢慢向舅舅家走去。
舅舅的院子里,除了少了那棵大榆树,变化不大,只是远不像从前那样整洁了,姥爷在世时,晚年不大参加集体劳动,每天把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西北角落放柴草 的土窑坍塌在那里,形成一个土堆,东北角落处圈羊的窑洞也不复存在,换成了一间临时搭建起的简易棚子,正房从外表上看,更加破旧不堪。
看得出,生活的沉重 负担,使舅舅失掉了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农业合作化的结果,早将中国老一代农民的发家梦彻底击碎,未来只有靠年轻一代去重振家业了。表弟也已二十岁上下,舅 舅的希望或许就在他身上吧。进到院里,大妗急忙迎出门来,身旁跟着一个秀气的十岁左右的女孩,这是她的女儿,女孩和我头次见面,含羞地叫了一声“表哥”, 我们一起走进屋里。
不一会,三妗也从外面的院子里进来了,接着来了杨家不少的人,有和我从小在一块儿玩耍的两位表叔,他俩和我年龄相差不多,是奶奶的侄 儿,也是母亲的堂弟,大表叔则刚从地里赶回,三个表婶,只认得大表婶,其余两位,都是我走后嫁过来的,第一次见面。正在和两个新见面的表婶说话的当儿,一 个高个子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劈口问我:“表兄还认得我吗”?仔细一看,这不是满有表弟么,我走时刚结婚一个月,他是我母亲堂兄的儿子,大姥爷的长孙,随他 进来的还有他的母亲,和我母亲的年龄相差不多,我忙叫了声“大妗”,并请老人家上炕。满有的媳妇,只是那年在结婚典礼上匆匆见过一面,此时已是几个孩子的 母亲,对她几乎毫无印象了。这时,大家东一句西一句问起我的情况,我便把自己前后两案都已平反的事,简要向他们做了介绍,他们听说我第一案也平反,不久可 以去东北上班,都为我高兴。“这下可好了,总算熬出来了,上班后赶快娶个媳妇,先成家吧,这回有了条件”!三妗代表大家向我表达了亲戚们的愿望。这时,窗 外也聚集了不少人,大都是年轻的妇女和孩子们,面孔陌生,他们一定是听说这个当年差一点就被枪毙的人,竟然活着回来了,用种种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仿佛我 是天外来客似的。
大妗和三妗商量了一阵,忙着烧火做饭去,她们都去了外面的一处院子里,那是三舅的家,自从二姥爷二姥娘去世后,四舅因在城里工作,原来的窑洞便由三舅住 着。我和大家谈论了一个多小时,快到中午时候,人们渐渐散去,最后只剩我和大舅。他本来在地里干活,听说我来了,便赶着牛,扛着犁提前收工回来,如今不像 合作化那阵,多咱想回来都行。大舅是个不善言谈的人,人多的场合向来不吱声,当屋里只剩我们两人时,他方才慢吞吞地说道:“真想不到啊,大家都以为这辈子 见不到你了,唉,要是你姥爷姥娘都还活着,该有多好啊!四年前死时还惦记着你,尤其是你姥娘,快咽气时,嘴里还在念叨着你的名字”。说到这里,他哽咽着, 不再说下去,我的泪水刷刷地往下淌,很长一阵,两人谁也说不出话来。
的确,这里留下我太多太多的记忆。土改以后那几年,姥爷养着一头母牛,后来产下一头十分健壮的小牛,那牛犊一直和我非常要好。五十年代初,又买了一匹棕色 的马,每年夏天,他一个人放不过来,总是由我和他共同放牧,因为他还同时割草,以备下雨时牲口食用。那时,父亲做货郎子,多在阳方口一带,不常回来,母亲 独自在家种地。生下大妹后,母亲忙时,我在家照看大妹,不忙时,恰好又是放牲口的季节,便长时间地呆在姥娘家里,和姥爷一起早出晚归。当时农村的小学校, 管得并不严,每年夏天孩子们去得不多,大都在帮大人干活。这给我常住姥娘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只有到了冬天才不能缺课。
中午吃饭时,两家合在一起,表示我们难得的团圆。三舅上午从学校回来后,简单和我打了个招呼便走了,估计是到城里去买菜去了,同时,他也把两个表妹叫了出 来。吃饭的时候,我提出一个问题:“这些年,我给大家的影响恐怕不少吧”?大舅随口说道:“我们种地的人还怕受啥影响呢,反正就是受苦和受穷”。三舅却 说:“要说受影响,也不是没有,都是有些村干部故意制造的,比如你二表妹,从小有搞文娱活动的特长,那年峙峪煤矿成立宣传队,要她去,村里开介绍时,有关 社会关系,首先写着表兄是‘现行反革命’,却撇开她的舅舅不写,因为她舅舅当时在部队里是团级干部。社会关系,舅舅重要,还是表兄重要,他们难道不知道 吗?偏偏有些干部,就是怕你走出去以后比他们强了,巴不得大家在一起受罪。
你二表妹的事,幸亏当时煤矿没太在意,现在调到了神头发电厂,总算有了一份正式 工作。”我也问了三舅的情况,他依旧当管理员,只是抱怨说,现在的工作比过去难做多了,校长、书记的亲戚安插到学校不少,尤其是食堂里很不好管理。在我和 三舅说话的过程中,大舅每隔一会儿就往我杯里添酒,还不断催我喝,他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用催我喝酒的方式,间接表达着一种深切的关爱。也不知是喝得多了 一点,还是因为看见了我,他显得特别高兴,慢慢也打开了话匣子:“总之啊,我琢磨着,这世界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能想到农业合作化还会变呢,如 今不是又退回到单干了吗?不管上面叫包产到户,还是家庭联产承包制,总之,土地又归咱们自己种了,就像你小时候那阵,人是自由得多了,想种啥就种啥,想啥 时候干就啥时候干,也不用请假什么的。大概你也听说了,从前的地主富农都摘了帽子,大家一样了,你们过去因为成分受了不少罪,今后再也没有四类分子了”。他呷了一口酒,眼圈有些发红,深深叹了口气说:“唉,可惜你姥爷姥娘没能活到今天,要是他们看到你回来,真不知道会有多么高兴啊”。气氛一下子沉重 起来,三妗是个反应敏捷的人,忙把话题岔开:“听说你爷爷奶奶都还健在,他们比你姥爷还大吧”?“是的,不久我就动身去内蒙看他们,毕竟人老了,有今天没 明天的,他们总算把我盼了回来”。
饭后,我们简单休息了一阵,三舅不知被谁家叫了去。他在当管理员的时候,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不少修理技术,回到村里那几年,经常给人们修锁子、配钥匙、裁 玻璃、修自行车等。现在虽然上班了,每次回来总有人要找他。大舅则陪着我,在村子周围慢慢转悠着。他虽然没有念过书,不懂得许多大道理,但从年轻时就是农 业方面的把式,曾经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一心想发家致富,还准备着在他手里修建一处大瓦房院子。可是,生不逢时,他的梦想,被合作化的车轮碾得粉碎。如今 人老了,尽管又回到了从前单干的时代,梦想却再也回不来了。况且,这时候,农民心里毕竟还不踏实,担心以后再变。当我们走到村子北面时,我很想拐向东北方 向,去坟地看看姥爷姥娘,却不便说出口,我们这里的乡俗,外人不能随便进入坟地,女儿出嫁后不准按时节祭奠父母,外甥是随女儿的,再亲也不能算作家人。我 想,大舅在这方面一定还恪守着旧规矩。他见我不住地向那个方向张望着,明白了我的意思,对我说:“你姥爷姥娘埋在了西北上曹沙会村那面,坟是新建的”。我 也再没提什么要求,跟着他慢慢回到了家。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方才告别了舅舅家。那时,三舅也正准备回学校去,他执意要用自行车带我。原本打算边溜达边看看,好歹只有几里路程,不一会儿就会回去的。拗不过他,只好由他带着,谁知,他一直把我送到离大妹家很近的十字路口。
一百三十一
从舅舅家回来的第二天,依旧是个春光明丽的日子,妹夫昨晚上夜班,正好在家里看孩子,大妹带上我回村给父亲上坟。所有纸张等用品,她在前一天已备办齐全。 塞外的春天,雨水极少,路上到处是尘土,骑车显得十分吃力,大妹带着我,不久出了一身大汗,我们走得这条路,平日里行人很少,为的是直奔坟地,免得绕路。 她骑得实在疲乏时,便下车慢慢推着走。“你还记得父亲的坟地吗”?她问我。“怎么会不记的,绝对不会搞错的”。我答道。按我们当地的习俗,出嫁女子不允许 进入坟地,因此,她也多年没有去过那里。这些年,只有二弟不忙时,碰到清明节或七月十五,上上坟。一路上,我又想起那年离家去学校时,走出村外,父亲对我 的嘱托,希望在他走后,我能和母亲共同把弟弟妹妹拉扯成人。为此,毕业后,谢绝了一些好心人给我介绍对象,准备三十岁以后结婚。后来被人诬陷,送回村里管 制时,虽然和母亲把弟弟妹妹拉扯了几年,但比起我带给母亲的痛苦来,实在是微乎其微,我又一次深深感到,辜负了父亲的嘱托,实在有愧对亡灵之感。
过了厦阁村,很快到了坟地。严格说来,我家根本没有坟地,父亲去世后,村干部随便指定了一块地的地头。那一带,坟地比较密集,尤其是我们吕家,各家的坟地 大都在此处,离老祖坟不远。但其他人家的坟地,都经过阴阳先生察看。小时候,跟着父亲给曾祖父上坟时,知道了老祖坟,曾祖父被埋在了坟的末端,以后各家都 看了新的坟地。唯独爷爷,在同辈兄弟中排行较小,一直未看坟地。当我把祭品都摆在坟前时,大妹站在远处问我:“对吧?别弄错了”。我说:“不会的,你看往 西北方向走十几步那个坟,是吕有才三大伯,他死时我正在村里,是我帮着打发的,他上面那个坟比较新一些,估计是大爷爷和大奶奶,他们都是我走后去世的,还 能有错”!大妹始终不敢走近,我招呼她:“你也进来吧”。“不是出嫁的女子不能进坟吗”?“哪有那么多穷讲究,还不都是人规定的”!她踌躇了一会,还是没 有进来,据她说,怕对我们弟兄们不好,我也不再勉强她。上过香后,点起五色纸和各种冥钞,嘶哑地喊了一声:“父亲,我回来看你啦”,便把头锥在地上,痛哭 起来。此时此地,真不知从何说起,真希望世上有鬼存在,要是那样的话,父亲一定会看见我。烧完纸后,在坟前坐了很久,算是我陪他。父亲啊,你还认得我吗? 你的不省事的儿子又回来了……
按照大妹的安排,上完坟后,回村看望一下本家的长辈们。本来,我是不打算回村的,母亲走后,村里什么也没有了,那里留下我数不尽的伤心的记忆,但按照传统的习俗,应该回来看看族内的伯伯叔叔们。
进得村来,只见村东头建起几排新窑,再往里走,便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在我小时候,各家的院墙都很整齐,后来年久失修,先是墙皮脱落,慢慢的,这里一个口 子,那儿一个豁子,多数人家的院墙早已不成其为墙,。合作化以后,按月分粮,每月分得那么一丁点,全放在住人的屋里,院墙失去了防贼的功能,人们很少去修 补它。
最东边的一户人家,仍然是二大伯吕元喜的住处,,这时节刚刚开始春播,尤其是年长的人大都在家里闲着。二大伯比以前苍老了许多,满头白发。对于我的归来, 他比其他人更感到高兴,“阶级斗争”最猖獗的那几年,我和他每次都是重点斗争的对象,二大娘紧紧抓着我的手,只说了一句:“你们爷儿俩总算活过来了”,就 再也说不出话来,不住地擦眼泪。二大伯用宽慰的口气说:“你妈的日子也好过了,我每次去看你金枝妹妹,都要顺便看看你妈,她走好了,当时我们都劝她离开咱 村”。二大伯的女儿和母亲住在同一个村里。“现在可好了,再也不提啥‘四类分子’了,大家都一样,土地分开后,人比以前自由多了,真想不到啊,咱们还能有 今天”!二大娘送我出来时还不住地这样说。
接着,我们挨家挨户地看望。父亲的同辈兄弟共有二十多人,除了在外地的,村里还有十几户,因此,每家只能呆很短的时间,也就是礼节性地看望一下,大家见个 面,让他们都知道这个不省事的子弟活着回来了。村里还有几位本家的姑姑,也需要看看。一直到中午时分,方才把村东边一带的看过。过去,村东边住的大都是吕 家,只有两户赵姓人家和一户姓李的,也都是多年的老邻居,不能不看。尤其是李致忠家,他是我的表叔,其妻又是我的表姐,“文化大革命”中,爷爷被撵回来, 很长时间就住在他们院里。
本打算一直继续下去,这时遇到了吕立,他是我的堂弟,只比我小几个月,从小一起耍大,当年他家也是“四类分子”,正所谓同病相怜吧,他把我拽回家里,“其 他人吃过饭再看,咱们先喝酒”。接着,吩咐他的三弟,马上把成年的几个堂弟都叫过来,中午大家一起喝酒,庆祝大哥活着回来。看得出,他非常高兴,并把他的 媳妇介绍给我:“这是你走后,也就是七二年吧,临县遭了灾,我去那里领回的媳妇”。随即又对他媳妇说:“这就是我常和你说的那个‘反革命’大哥,咱吕家目 前数他有文化,他是咱们的秀才啊”。弟媳很有礼貌地叫了声“大哥”,忙着烧火做饭去了。
午饭时,众兄弟问起我今后的打算,我说还回原单位上班,当他们得知我第一案也平反时,更是兴奋得不得了,每人斟上一杯酒,要和我干杯。许多年来,生活在孤 独的环境中,难得有今天的欢欣。看着这些堂弟们个个都成了家,回想年轻时“光棍村”的情景,自有一番今昔之感,看来,时代真的是大变了,那些年我们去哪里 喝酒呀!
下午,吕立安排他妻子和大妹在家,他陪着我由前街到后街,把所有吕姓人家的伯父、叔父和姑姑们都看了,也顺便看了依旧活着的当年的“四类分子”们。这时, 春播正在进行,一些中年人赶着毛驴车往地里送粪,多数人都还闲着,我回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全村,走在街上,到处是人,包括昔日的村干部,都和他们一一打过招 呼,只在曹建忠家里呆了一阵。当日民兵连长,脸上那股生气早已消失殆尽,奋斗的终于结了婚,听说生了好几个孩子,日子依旧过得紧巴,算是不挨饿了,但仍然 缺钱花。随后又特地去了黄裕明家里,他的老伴眼睛不大好,一时间竟然没有认出我,问起当年的老搭档,她方才醒悟,“是你啊那娃,你大爷前几年就走了,唉, 苦命啊,他没赶上现今这吃饱饭的日子”。我安慰了老人家一番。想起过去,我们在一个小队里,无论掏茅厕、抓粪、拉炭,还是铡草,我和黄裕明总是一对,也可 以说是忘年交吧。如今他早早走了,我心里自然有一种酸楚的感觉。
正当我和吕立往回走时,在一堵石头墙边看到了李忠信,这个往日神气十足的大队长,自然也苍老了许多,目光有些呆滞,我快步走上前去,抓着他的手说:“二 叔,你好,还认得我吗”?他一时没有回过神来,表情甚为尴尬,简直不知说什么好。“身体还可以吧”?我又问了一句,他只“嗯”、“嗯”了两声,我随即松开 手,向他点点头然后走开。“那号人,别理毬他”!吕立忽然甩过一句话来。此人在村里名声一向不好,当兵回来后,先后在大队当过支书、大队长,被他打骂过的 社员很多很多,背地里人们称他“赖肺子”,也就是通常说的坏心眼儿。自从土地分开后,听说他成了“没人理”,每逢走到人们面前时,有些人总爱用讽刺的口吻 挖苦他当年的骄横,久而久之,他便远离人多的地方,深陷在孤独中。据说,当年判我时,他拿着一张大纸,挨家挨户要人们盖章,要求杀我,除了吕姓人家,他一 户不拉地命令人们盖上章,然后交到了军管组,又听说,当我被判死缓后,他还十分遗憾哩,真不知他和我之间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仇恨,难道仅仅因为我念了十几年 的书?
回到吕立家里,他首先埋怨我:“像二聋子(指李忠信)那号人,今后见了面好眼也别看他,那些年搞‘阶级斗争’,好多坏点子都是他出的,恨不得把我们这些人 统统整死”!我解释道:“都过去了,毕竟那是当时的政策所致,他们只是充当了打手,现在为啥不欺负我们了?所以,对这些人大可不必计较。一个时代嘛,二聋 子不来整我们,或许还有三聋子、四聋子出来,我的观点,过去的这些事,对一个小小的村干部,完全可以原谅”。“到底是你们念了书的人能想开,不过,话说回 来,老天有眼,他现在比咱们差多了,农业社把他惯成一个懒人了,劳动方面他已远远不如别人,晚年又生了一个愣货,患有严重的神经病,也算是报应吧”。吕立 说过这些话,他的妻子早已
端上茶来。我们边喝水边聊起村里的情况,这十几年来,已有几十个人离开了这个多灾多难的世间。
傍晚时分,我和大妹告别了吕立一家,回到城里。
一百三十二
母亲所住的村庄叫窑子头,在我很小的时候,这个村子是三区的区公所,父亲那年从口外回来接我们,被民兵捉走就关在这里,听说这村子很大,我一直没有来过。 现在来了,给我的感觉也就是大一些,没有其它的特点,和我们这一带乡间的其它村庄实在没有什么两样,人们住得也都是土窑,而且南北距离拉得过长,松松散 散,很不集中。多年来,它曾作为公社的所在地,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布局,这里两户,那儿三户,各自为阵,参差不齐。母亲住的院子,坐落在村子的中部偏 东,背后是过去的公社,如今的乡政府所在地,乡政府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邮电所和储蓄所,在邮电所的西边,是乡里的供销社,门前老是聚集着人,常有附近村庄 的农民来这里购买一些农用物资。由此看来,母亲所住的院落,还算是这个村庄的繁华地段。院子里有正窑三间,一明两暗,东边一间,二弟住着,西边那间住着一 位八十多岁的老妇人,她是母亲如今的婆婆。三间正窑东侧,有两间土房,紧靠着向东开的大门,房子处处呈现出多年失修的破落景象,一明一暗,母亲一个人住 着,大多数时间在这里做饭。院子的西墙处,是两间更不成样子的小土房,里面堆放些杂物,西墙过去,是从前队里的碾磨房,因此,院子里耗子特别多,甚至白天 也可以听到它们的尖叫声。
我来的时候,二弟新券的窑洞大体起工,还有一些零星的抹墙之类的工作要做,只留下两个匠人,不用管饭。这时,一家人尚未分灶,仍然吃着一锅饭。但是很少在 一起吃,每次饭熟后,母亲先给婆婆送去一份,因为老人行动不便,然后再给弟媳送去一份,她已经到了临产的时候,我和二弟、母亲便在土房的炕上吃,三岁的小 侄女有时跟我们在一起,有时又跟她妈妈在一起。我的归来,对母亲来说,自然是一大喜事,几天来,她显得格外有精神。听说,继父一年里回来两三次,平常的日 子还是她和二弟一家。这时,二妹已出嫁一年多,三弟在一所煤矿子弟学校教书,不常回来。每天,二弟早出晚归,多数时间不在家,四个女性年龄差异甚大,各行 其是,相安无事。
我回来的这两天,母亲整天处在兴奋之中,她有许多许多要说的话,往往又没有头绪,常常是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从她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得知她在我刚刚判刑后的 处境十分艰难。也不知我们的祖上哪辈子和李家有过矛盾。当时担任大队长的李忠信想方设法要把我们一家置于死地。当我判了死缓,留下这条贱命,他曾经遗憾得 不得了,他挨家挨户命令人们签字盖章要求杀我的希望落空后,把所有怨愤发泄在母亲身上,强迫她和男劳力干一样的重活儿,这些,母亲倒也能够接受,最令她难 以忍受的是那种冷嘲热讽的语气:“你了不起啊,生了个大秀才,竟敢和共产党毛主席作对,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是不是又把希望寄托在二公子三少爷身上 了”?等等不中听的话。她无可奈何,从来不敢还击一句,慢慢地却从这些话中领悟出一点,人家对她的另外两个儿子也很不放心,尽管他们还都没有成人。作为母 亲,她有一种特有的敏感,两个小儿子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我走的前一年,公社农业中学招生,村里去了十三个孩子,三弟考得最好,结果录取了除他以外的十 二名,连个农业中学都不能上。村里对这些人家的子弟一直不放心,是因为土改时他们分了这些人家的土地和财产,尽管有政府做他们的坚强后盾,一些人还是不放 心,生怕这些人家的子弟读了书有了办法,对其进行报复,因此尽量压制。说来真是有些杞人忧天,但农村的情况往往就是如此。五十年代,政策比较宽松,我蹦出 去念了几年书,充其量只是中专毕业,可村干部却一直耿耿于怀。等我回村后,仍然放心不下,可惜知识是无法没收的,便想方设法地折磨我。后来,我住进了监 狱,而且判的是死刑,想来他们可以放心了,可对我的弟弟仍然要严密监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开始萌发了要离开这个村子的念头。但当时的政策,尤其是户 口制度,早已画地为牢地把每个人固定在一个点上,想离开或迁出去是万万不行的,除非嫁人。
那时,正好我的一位本家五叔从平鲁回来探家,他是我们吕姓家族中 和我一样念过书的人,初师毕业,在平鲁县一所小学校担任校长,虽比我大四岁,母亲却很信赖他,认为他比一般人有见识。五叔得知她的情况后,坚决主张离开这 个村子,他说:“按理说,我不应该说这话,说这话,我那死鬼哥哥在地下也会恨我的,但我们顾不得为死人考虑,更多的要为活着的人着想,要为孩子们将来找一 条活路,你走吧”!五叔的话,她最听得进去。在这以前,大爷爷和几位本家伯父们也都曾这样劝过她,她总是拿不定主意,怕孩子们跟上受罪,如今五叔也这样 说。她初步决定了要走,接着又去姥爷家和父母商量,姥爷姥娘当时甚是为难,一方面他们心疼女儿遭受这么大的不幸,另一方面,姥爷又觉得对不起两代外甥,也 对不起自家的堂姐,于是又打发母亲去集宁和我爷爷、奶奶、叔叔商量。当时的情况,各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对于母亲的处境,亲人们都是爱莫能助。爷爷奶奶在集 宁没有户口,住在二叔家里,也是“黑人”,二叔已经够烦心得了,三叔则因为受我的牵连,无端被怀疑,刚刚从看守所放出来,工作尚无着落。这种情况下,谁也 没有更好的办法,都觉得母亲要走,实在是无奈的选择。母亲是那种办事情考虑比较周到的人,加之从小养成的尊重长辈的做人准则,凡事都要征得父母和公婆的同 意,否则是不会付诸行动的,她可怜他们,更不想伤害任何一个人。
大凡妇女们一旦提起改嫁之事,总有热心人从中作媒。五十岁上下的男子往往不易娶妻,只能从改嫁和离婚者中选取。给母亲介绍的是离我村二十里的窑子头村一个 人,姓柴,在大同矿务局下属的一个林场赶马车,和村里的车夫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属于市民户口,挣工资,也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吧。此人年轻时曾先后娶过三 个女人,都因为他母亲不喜欢中途离异。给母亲介绍的人说,条件还可以,只是婆婆难说话,挑剔得很。母亲全面考量,权衡利害,觉得人家在外面工作,每年回来 的次数有限,家里基本还是她和自家的孩子们,这样极好相处,等到人家退休后,孩子们也各自成了家,不会出现大的矛盾。至于婆婆比较难处,她则一点不担心, 他一向对人真诚,又生性勤快,相信用自己的真心,完全可以取得对方的理解,于是同意了这门亲事。
办完所有手续,柴老汉赶了一辆马车来接她和孩子们,把那些破衣被和几个瓮、罎都捆绑在大车上,准备起身时,被我村的治保主任王富和小队长黄继德拦住,理由 是交清罚款。一切阻拦都失败后,眼看着多年被欺负的对象就要离开,甚至是远走高飞,这些心胸狭窄的村干部,所使出的最后手段就是讹诈。还是父亲在世时,我 们住的窑洞后面有一眼井,是爷爷年轻时打下的,后来农业社要利用这眼井浇地,所用水兜子较大,嫌我们过去的井桩过细,便拆了下来,换成粗的,换上去的井 桩,原先是花轱辘大车的半截废轴,碗口粗,三尺多长,泥在井台里,上面用一块很大的石头压着,辘轳就安在这根轴上。几年后,井里的水渐渐减少,队里也不派 人掏泥,于是报废了,井台也坍塌,父亲先是把那半截破轴拿回家里,后来觉得不妥,送到了队里,队长嫌他多事,不就是半截破木头么,硬是让他拿回去烧火算 了,队里要那破玩意儿干啥!以后一直横在院子的角落里。农村里不缺柴禾,谁也懒得去劈它。等到母亲改嫁时,真是磨道里找驴蹄印儿,总算抓着一个把柄,声称 这半截破轴是偷的,罚款七十五元。面对这种极不合理的敲诈,忠厚老实的继父,着实无奈,他也很同情母亲的不幸,知道争执也是无济于事,于是拿出两月的工资 给了王富。他们再也找不出任何理由,只得放行。快出村时,母亲想起过去种种被虐待的事情,不觉辛酸齐来,大放悲声,三弟和二妹也一齐嚎啕大哭,撼天震地, 简直像是出殡一样,观看的村民无不动容……
后来,每逢和继父谈起这些往事,他总是说,你们村的干部咋那么赖!
- 关键字搜索:
- 血色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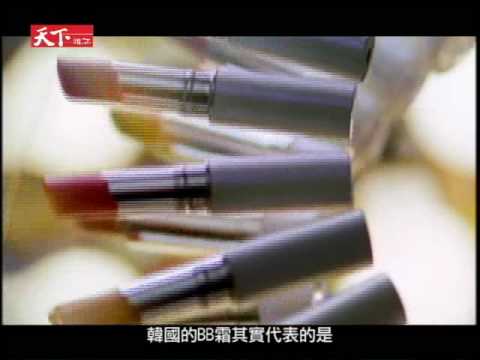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