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一百
一九七五年的夏天,在大中队所有领导在场的情况下,把我一人叫到工地办公室,下达了一项极其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监狱领导决心改造二大队单机加工阀门的现 状,拟建一条全自动机加工流水线,图纸已经拿回,正布置模型组日夜加班赶制木模,要求我们组务必在四十天内,完成所有组合机床的毛坯铸造任务,大件约有五 十多个,条件是需要多少人,车间内由我挑选,每天收工后不午休,不参加学习,一直干到晚饭时,必要的话,申请夜间加班。最后,丁大队长问我:“还有什么困 难,你提出来,领导协调解决”。我略一思索,只提了一条:“所有这些大件,都需干模铸造,咱们的烤窑太小,恐怕烤不过来,能否腾出一座回火炉,烘烤砂型和 泥芯,可能要影响部分阀门的回火进度”。“行,就腾一座回火炉,满足你们的要求”。大队长马上拍板,最后又叮嘱我:“务必按期完成任务,这是监狱领导对我 们一大队的要求,你一定要妥善安排,做到见缝插针,大小件穿插进行,千万不敢出现窝工现象”。说实在的,我并不是那种积极进取,想望减刑的人。但任务一旦 落在肩上,又从来不喜欢推三阻四,消极应付,总是千方百计去完成。人总要维护自己的脸面,何必让人说三道四呢。再说啦,监狱各级领导基本能做到公事公办, 不像农村干部,时刻都在找你的毛病,把你当做斗争的活靶子。因此,我也不能让他们感到为难。
回到组里,把任务介绍给同伴们,要求他们帮我物色几个能干的年轻人,大家很快拿出名单,报告了中队领导,一个由十人组成的精干的小组成立,张进忠带领着做 准备工作。我和零件生产调度员雷小厚一起到模型组了解情况。每当他们制成一件模型,准备做泥芯盒时,我们便把模型拉回,按其形状、大小,赶制专用砂箱。参 加这次突击任务的人,以前只干过漏模机造型,各种规格的砂箱应有尽有,他们连制作砂箱都不会,一齐跟着张进忠陈春生去学,我则预先熟悉图纸,带着两个人负 责下泥芯和合箱的工作。过去,这个组每逢铸造一件较为复杂的新铸件,下泥芯时,总要请木模制作者来现场指导,以保证位置正确,壁厚尺寸符合要求。自我来 后。这件工作就成了我的专职。在学校时,对制图课特别感兴趣,立体感较强,一直作为这门课的课代表,代替老师对同学们进行课外辅导,想不到竟然在监狱里派 上用场。随着模型进度的加快,根据大小、难易,穿插进行,尽量利用旧砂箱,以便节省时间。同时要求大家抓紧工作,力争在晚饭前或更早一些时间完成当天的任 务,避免夜间加班。我一向讨厌那种疲劳战术,用加班去获取领导的赞许,深知加一次夜班,几天下来都会疲劳不堪,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时值盛夏,每逢铁水下来时,热浪滚滚,同时安排了陈春生保证大家的饮水,不能上火。只要谁也不缺勤,相信一定能够按期完成。同伴们个个都是赤膊上阵,每天 收工时,浑身上下一片灰黑,比煤矿工人还要脏。而当我们进入澡塘,尽管此时水已很脏,大家泡在里面,脸上方才露出笑容。早上五点半开工,下午五点半收工, 除去两顿饭,近十一个小时的劳作,大家都很累。每天收工后,只觉得两条腿像灌上了铅,沉重得很,只有咬紧牙关,坚持着,有时互相说些打趣的话,甚至略带一 点荤味,引起一阵哄笑,冲淡了身子的疲劳。抽调来的年轻人,普遍比我小几岁,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相互之间根本不用像老犯人那样彼此提防,因此每天都能顺 利完成任务。随着新手的熟练,往往能在下午四点或更早些时候收工。收工后,名为整理一下场地,大家坐在一起,抽烟、喝水、闲聊,然后在澡塘里多泡一会,免 得回去早了还得学习。看得出来,这期间虽是累点,彼此心情还是愉快的。我想,应该给同伴们不断灌输一种思想,即使坐监了,也要经常愉愉快快的,不要钻牛 角,不要自找烦恼。我常记着监狱政委的一句话,“政府决不会因为你苦恼提前将你释放”,千真万确,没有人会可怜你的。与其苦恼,还不如高高兴兴,这叫黄连 树下吹喇叭——苦中作乐呗!
不知不觉间,一个月过去了,在第三十八天收工时,我们终于全部完成了任务。大家感到格外轻松。其间,大队、中队领导每天都要到现场了解情况,不断对我们进 行表扬,仿佛我们都成了劳改积极分子似的,由此,更深地体会到,什么叫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道理,一切都是无可奈何,谁叫我们活在枪杆子底下呢!
年终总结时,我们中的所有人员都受到了记功的褒扬,我个人则记了一次大功。这些都是入监以来始料未及的。但这一切并不能改变我的态度,从内心来讲,我不打算争取什么,只求日子过得安稳一些。
一百零一
做完组合机床后,临时抽来的几个人,除侯来小、高圣外,其余都回到原来的小组。我们组实际上增加了两人。侯来小的精明能干、手脚麻利是其他人谁也比不了 的。他脑子转得很快,无论学什么都能很快领会,的确是一把好手,可惜此人只读了小学三年。高圣虽然比侯来小有点文化,也是因为他爱看报纸杂志什么的,七零 八落捡来的一些知识,两人都没有正儿八经地读过几年书,这在穷困的乡下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他俩都比我小四五岁,名义上好像是我带的徒弟,实际上很快成了 知交,以至于许多年后,当我们都恢复了自由,尚有来往。
既然让我担任这个小组的犯人组长,便决心按照自己的意愿,营造一个与众不同的环境,使大家都能够比较舒心一些,最起码不要互相闹意见。为此,首先需要创造 一种良好的学习气氛,要大家努力学习技术。人一旦有了钻研的对象,便不再想那些邪门歪道的事情。我曾对他们讲:“我们都是来自穷困的农村,将来有一天假使 能够出去,谁还愿意回去种地。因此要利用年轻的时候,学一点技术,准备靠技术吃饭,或者留在此地,或者到小的厂里找份差事。听说晋中一带各县都有不少小翻 砂厂,如果我们学得一手过硬的技术不怕没有人用。退一步言,就算将来用不着,起码它不吃你不喝你,也没有什么害处。而眼下,你能把握好质量,不出废品,给 自己也会少招惹麻烦”。我这样讲,丝毫不违反政策,大家都很赞成,陈春生也在一旁帮腔:“你们几个难得有一位好老师,想学铸工技术,学看图纸,他都能教你 们。我也是那句话,即使将来用不着,起码没有坏处呀”。从此以后,整个小组迅速行动起来。收工后,经常把一些图纸带回号房看,政治学习的时间,大都成了技 术学习。我并不从投影开始详细讲解原理,只是结合实际,先简单讲讲再让他们对照模型比较,最后在我们造出毛坯后,让他们自己比对实物,弄不清的地方,再加 以指点。这种办法,效果比在学校上制图课要显著得多,立体感极强。甚至连一向稀里糊涂的李墨林,也掌握了看图的基本要领。那时,车间订着一份《铸工》杂 志,很少有人问津,我和公务组调度员打过招呼后,这份杂志后来索性归我们组,每有实用的东西就念给大家听,不懂的地方尽量讲解清楚,大家越学越有兴趣。遇 有指导员检查,发现我们在政治学习时看图纸,也不说什么,我常常主动解释,借口最近任务忙,需要首先熟悉图纸,他表示理解。前面说过,这里的干部,工作重 点是保质保量地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我正是瞅准了这一点,才敢于把学习技术放在政治学习的时间里。
这年冬天,接受了铸造c620车床的任务,我把所有图纸通统找来,供大家学看,很快提高了大家的识图能力,尤其是侯来小,复杂的图纸也能看懂。从此,我有 了得力的助手,生产中的许多事情不用亲自过问。几年来,看到这里的不少老犯人十分保守,一点技术都怕别人学会,衬了自己。我曾经嘲笑他们,劳改还怕人衬, 那就只好一辈子坐监了。我则是尽量教会别人,使自己轻松一些。而且这样做,还有一个极大的好处,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关系亲密,彼此心情都很愉快。
十几年后,这些人都走出了监狱,有的留厂,有的在附近的社办工厂(后来改为乡办工厂)找到了工作,他们依靠技术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穷困面貌。当然,这只是后话,详细情况,这里就不再叙述了。
一百零二
紧接着,需要着手改变的就是车床的定额问题。这问题实在是太棘手了。从前,这个组互相闹意见,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硬把定额直往高里提,借以显示其靠近政 府,改造积极,以至于最后给自己套上绳索,谁也很难完成任务,有时为了赶时间,常出废品,质量得不到保证。张进忠和陈春生在这方面最有体会,尤其是张进 忠,他把床头箱的任务提高到五小时,现在忙得不亦乐乎,八小时才能勉强做完。陈春生年老手慢,更是无法按定额完成。这一切都是长期存在的实际问题,我曾和 侯世枢说过,他不敢动,因为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定额只能上不能下,和领导说也是白搭,要改变难度极大。一旦报告领导,领导会说:“先前人家能完成,咋现在 完不成了”?思来想去,还是不动为好,免得犯错误。最后,采取了一个补救的办法。每人同时配做一些零星的维修件,比如说,一个小小的皮带轮,半点四十分可 以完成,记工时记成两小时或更多一些时间,只要当时无人说穿,过后谁知道这是多么大的皮带轮。我想,照顾了大家,使得众人都能完成任务,想必没有人会找麻 烦的。就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还好,平安无事,再不用像以前那样手忙脚乱还完不成任务,大家自然都很高兴。
还是陈春生心细,很快就发现我的做法,有一次悄悄跟我说:“你这样搞,我也知道,是为了大家好,可是人要是太心眼儿好,往往也会吃亏,万一以后有人揭发, 领导追问下来,可要吃不消。从前张立才当组长时,吃过这些人不少亏,你要多长个心眼儿,提防着点”。我明白,他指的是张进忠,怕他汇报。张进忠在这方面固 然有点吹毛求疵,好搞小动作,但我一直对他不错,想来也不至于。我只好对陈春生这样说:“过去的定额的确非常不合理,应该废除,况且,我们平时做得大多数 是各队的维修件,有时只有一两件,你说怎样定定额,目前也只好这样凑乎了,以后有机会再说”。
过年后不久,刚刚释放完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党、政、军、特人员,接着来了一批新犯人,大队为了保证质量,准备成立工艺组,干部中有人提名要我去,在一次组 长会议上,我向领导推荐了张进忠,理由是:一、他比我干得年长,更有经验;二、他年龄大了,又做过手术,应该先尽他。大队采纳了我的建议,马上调张进忠到 工艺组,每天负责检查砂子的干湿,在车间里巡视,发现谁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及时帮助解决。张进忠本是个虚荣心极强的人,得了这份差事,成为技术人员,自然 喜出望外,他听人说是我推荐的,对我十分感激,每天一有空闲,便回到小组的场地上和我闲聊。我俩在一起也有四年多的时间,同住一屋,同吃一桶饭,岂能没有 感情!他曾因割去生殖器,每次洗澡时,总是用毛巾捂着那地方,常为此感到自卑。我一向把他当老师傅看待,彼此相处得不错,同是天涯沦落人,是我对同伴们的 基本态度。
也就是这年春天,中队长换成一位姓于的,新来的指导员姓阎,两人都已五十开外,一段时间观察后,这两人都喜欢安然无事,最讨厌犯人互相间闹意见。加之他们 刚来,对生产很不熟悉,我便下定决心,自作主张将车床的所有工时定额全部废除,在组里也未对任何人讲过,记工时只按照实际操作登记。从此,我们小组每做一 件产品,都要把质量放在首位,力争不出一个废品。任务忙时,没有定额同样加紧干,任务少时,当然可以吊儿郎当一些。加之工艺组成立后,雷小厚调到那里专搞 设计,他过去管的零件生产调度和模型库房,由我兼任,不算公务组人员,也不到办公室去,仍旧留在组里,无形中给我们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每当任务少时, 便和同伴们进入那个几十米长的木模库房,一边慢吞吞地整理模型,一边悠闲自在地聊天,图个轻松。当然,我们从来不做违规的事情,因为我一向主张不求有功但 求无过。生产上,丝毫不得马虎,学习方面则尽量应付,组内永远保持同心协力,和睦相处,互相多一些照应,营造一个小小的安乐窝。总之,该动真格儿的时候, 大家拧成一股劲,吃点苦并没有什么,该糊弄的时候,应付、凑乎着去办。这或许就是犯人们常说的“劳改经”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一天犯人,自然要念一 天“劳改经”,否则,怎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呢?
一百零三
清明节刚过,正是那种乍暖还寒的时节,传来了“四五”运动的消息,我的热血突然沸腾起来,看罢报纸上的报道,一时冲动,把帽子高高举过头顶,在上面转了几 圈,不由自主地喊出:“向勇士们致敬”!其时,伙伴们刚刚收工回来,有的去打开水,有的上厕所,谁也没有注意我的表情。躺在炕上的李有晋是熔炉组的搪炉 工,和我们同住一间号房,冲天炉打炉后,才出去工作,他上的是前夜班,看我激动的样子,压低声音提醒我:“不敢瞎说,小心吃家伙”!我笑了笑说:“放心, 咱们周围没有那号人”。接着把报纸上的话念给他听:“秦皇的统治已经一去不返,中国人民再不是那么愚不可及了”。“听听吧,我们的人民终于觉醒啦”。“那 顶屁事,咱们还不是一样坐监”!李有晋没好气地回答着,我理解他的烦恼。陈春生也简单把报纸看了看,随即发出一声叹息:“唉,我看咱们是完蛋了”!这话分 明是对李有晋说的。早在上年四月,政府先是释放了在押的所有国民党战犯,本监狱当时放了四名将军级的人物,包括我们经常看见的马路兵团司令。那是个身材魁 梧的老头,听说叫熊新民,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长官兼七十一军军长,在监狱里,因他是打扫马路组的组长,每天扛着大扫帚从各条路上走过,许多犯 人都知道他的大名,戏称其为马路兵团司令。释放后,先是到了北京,统战部安排他们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最后回到老家常德市,做了一名政协委员。消息是否属 实,我也很难说,估计是从干部那里传进来的。当时虽然仅仅放了四名,分明是个良好的开端。到年底时,果真传来更加振奋的消息,释放在押的所有国民党县团级 党、政、军、特人员,本监狱放了一百余人,当时就沸腾了,出去的人,每人发给棉衣一套,零花钱一百元,集体参观了大寨,听干部们讲,凡能工作的都要给予适 当的安排,和我很要好的关益三就是这次释放的。而且,这次释放,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获释前,个别人在禁闭室关着,也一起走人。释放国民党县团级,给许多老 犯人带来了一线希望,因为紧接着在全监狱进行了营连级的摸底登记,陈春生和李有晋都已有名在册,只等待着上级的命令,对于一些担任组长的人,中队已经配备 了接替的人。但就在这时,上面接二连三地出事,先是周恩来逝世,接着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运动,随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参与的人涉 及各个阶层,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政局动荡不安,让那些曾经期待出去的人忧心忡忡。邓小平的被黜,使这些人失望的情绪与日俱增,眼看就要和亲 人团聚,结果却不得不泡汤,如果以后让热衷于“阶级斗争”的那帮人上台主政,简直看不到一点希望。
此事本来与我干系不大,但我一直很关心,一则看到难友们获释,打心眼里替他们高兴;二则它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四五运动”被镇压后,又是评《水浒》, 批投降派,又是针对着已经去世的周恩来,说什么“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以那样嚣张,是因为背后有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在撑腰”。一时间,风雨凄迷,真不知道 上面要干什么,宫廷斗争的血腥味已经传向民间。国家的命运尚难预料,犯人还有什么出路?至于我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幻想,在这风云突变的时候,反而显得平 平。因为不管政策怎样变动,目前也不会放我,当局可以宽大一批历史犯,却绝不会饶恕“现行犯”!
不过,“四五运动”后,我的心却长久地不能平静下来。隐隐感到,自从林彪出事以后,军权落在老干部手里,这使权欲熏心的老头子甚为震怒。林彪是他钦定的接 班人,出那么大的事,一定使他难堪万分,一时无颜面对昔日的下属。经过几年后,他必定要反扑,大权一日不全部落入毛派手里,他就一日不会善罢甘休,因为他 要的不是集体领导,而是真正的毛家王朝。面对这样动荡的政局,作为劳改犯,我们自然也有失望和迷惘的时候,尽管这一切与我们相距甚远。这次政治学习,只是 照本宣科地读读报纸,极少去讨论,领导多次动员、催促,总不见效。比起批林批孔那阵,多数犯人的情绪更加低沉。我则是每天把报纸的角落里也要搜索净尽,希 望从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看看局势究竟向何方发展。一时间,年轻时那种忧患意识又在心底里悄悄泛起,多灾多难的祖国啊,难道你还要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 中?你早已是满目疮痍,莫非还要继续烂下去,直到病入膏肓?……啊,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第十一章 曙光在前
一百零四
九月里的一天,农历刚刚过了中秋节,天空晴朗无云,气温依然偏高。午睡起来,大家都坐到院子里学习。这时,除了造型五个组、铜炉组和模型组收工外,其它组 仍在工地上劳动。铸造车间向来都是这样,收工出工时间参差不一。院子里只有造型组在应付着学习。模型组在楼上的屋子里。大约四点半左右,也就是我们刚开始 学习半小时吧,大门开了,浇注组的人们收工回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从青海省来的魏占海,细高个子,三十岁上下,胳膊上挎着洗完澡替换下的脏衣服,他不是直 接回自家的号房,而是直奔我来。他将两手围成圆弧,嘴贴着我的耳朵低声说:“报告你一个重要消息,毛老头死了”!说罢对我微微一笑,然后走回他的号房。与 我邻座的李墨林好奇地问道:“魏占海和你说啥来着,我好像听到有什么重要消息”?我赶忙否认,随口诌了一句:“哪有什么重要消息,他说,明天大灶上要给咱 们吃猪肉包子哩,怕影响咱们学习,所以只悄悄跟我说了”。李墨林是个贪吃的人,只好顺着他的爱好,先撒个谎,搪塞过去。这等消息,在未经公开传达前是不能 随便说的,何况院子里坐着这么多人。许多年来所等待的不就是这一天吗?,但在表面上必须镇静,装作没事人一样。从今往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或许会走上 一条新的道路。这时,我的脑子里早已是浮想联翩。暴政结束后,作为其反动力,按照一般的历史规律,总要有一段清平宽松的年月,后来者对于暴政时期的种种弊 端早就看在眼里,只是敢怒不敢言罢了。所以,改变以往的极端做法,完全可以预期。我相信,当今时代,很少有秦二世那样的傻瓜蛋,非要彻底走向灭亡不可。
整个下午的学习时间,脑子里不住地想着有关毛的死亡,相信它是真的,一定是魏占海在工地上听到了大墙外面的广播,否则他不会也不敢这么说。联想到前一阶 段,从报纸上看到老头子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时的照片,神情呆滞,无精打采的样子,看来真的死了。古今中外,曾有过多少不可一世的铁腕人物,最后都未能逃脱这 一关。曾经有人预言,说毛可以活到一百四十岁以外,看来都是虚妄的。
这天下午的学习,没有读报,大家只是默默地坐着,不时有人看看我,对于魏占海和我说的话,他们肯定也都怀疑。但我不能说,万一消息不可靠,被谁汇报了,那 可是大问题,多年来对领袖人物的大力宣传,在各级干部中,甚至在一般群众中,都把毛给神化了,什么“大救星”、什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 导师”、“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等,不一而足。长期的愚民政策,导致许多人把毛泽东当做神圣一般看待,就是死了,也不是小民们可以随便议论的。 何况,我们还没有听到官方的正式通报。但不说并不等于不想,连想也不准有,常常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事实上,思想这东西永远无法没收,相反,越是管制得 严,人们越要去想,越是不让人们思索的问题,人们反而越思索得更多一些。
毛的去世,正标志着一个热衷于斗争的时代的结束。从“镇反”、“肃反”、“全民整风”,到“反右”、“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二十多年来,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先是针对国民党的残余人员,紧接着矛头对准了知识分子,把他们大批大批地打成“右派”,发配的发配,劳改的劳改,有些人留下来继续使 用,也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在沈阳读书时,学校就有几位“右派”老师,连说话的声音都很低,唯唯诺诺,从来不敢跟别人开玩笑。斗罢党 外人士,新的阶级敌人只有从自己营垒中去寻找了。于是,彭德怀出来了,刘少奇也出来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原先是共产党功臣级别的人物,一夜之间,都成 了阶级敌人,“斗、斗、斗,不斗则修”,大批老干部,从中央到地方都被打倒,整个国家陷入动乱的泥潭,大家都在高喊着斗争的口号,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的破 坏。
一个时期以来,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集体领导的原则被废弃,最后竟变成了一人专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每隔一段时间,发布一条“最高指示”, 作为当时的行动准则,真不知道,这“最高指示”和封建帝王们的圣旨有什么区别!原来,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仔细分析,充其量还是历代的改朝换代者, 脑子里装的依旧是皇权思想,这种人,何时有过人民公仆的意识?他们往往驾凌于民众之上,又何时受过监督和制约?这种人老子天下第一,只有他说了算,别人只 能臣服与恭顺,国家成了个人的私有财产,下属官员只能唯唯诺诺,照办和执行,决不允许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一个铁腕人物的逝世,往往预示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君不见当年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后继者难道还会置国家的经济于不顾,仍然疯狂地搞阶级斗争,我想应该收敛 收敛了,即使维系毛的做法于暂时,今后非放弃这套专制手段不可。谁也知道,一个国家,经济不发达,把阶级斗争搞得再热火朝天,轰轰烈烈,永远不可能富强起 来。老百姓居家过日子还常说,“没钱打不回油来”,一个国家,光靠专政和镇压异己,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一盘散沙,注定它永远是一个穷国。所以,“阶级斗争 永不熄灭”的说法和做法,必将被人们抛弃。只有这个枷锁彻底砸烂,像我这样出身的人,才有可能过上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才愿意走出监 狱的大门。
晚饭后,大家依旧像往常一样,有的闲聊,有的打扑克。七点钟,安在门顶上的小喇叭响了,我急忙招呼大家安静些,新闻联播开始了,果然正式传来了毛泽东去世 的消息,侯来小听了后,低声问我:“下午魏占海对你说的就是此事吧”?我点点头,接着他又放大声音,对我说:“李墨林还等着吃猪肉包子哩”。这时,李墨林 在院子里和人们玩得正起劲呢,我苦笑了,给侯来小做了这样的解释:“这么重大的事,未经证实,哪里敢说”!“是啊,就是证实了,也不能随便说”。后面这句 话分明是在提醒我。
- 关键字搜索:
- 血色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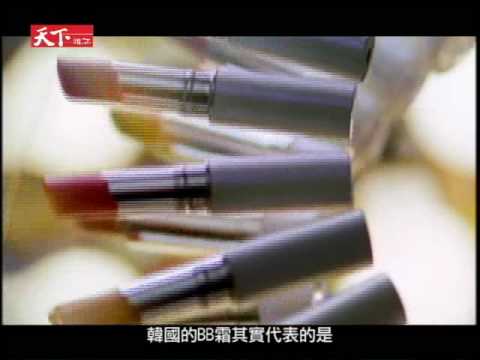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