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為有苦難,令我想起深夜的星星之火,我慢慢意識到,這片罕有人過問、卻多人到訪過的境地,其實一直存在著某股力量。(圖片來源:Pexels)
恐慌症可以說是焦慮症的其中一環,它的起因至今仍未有確定的研究分析,可能是生理、也可能是心理。發作時,常伴隨身體某部位的劇痛,症狀再接後出現,由微轉重:暈眩、發抖、癱軟、呼吸困難、喉嚨異物感、失真感(覺得自己的身體是假的)、四肢末端發麻、盜汗等等,平均持續二十分鐘,會達到痛苦的最大值,之後褪去。患者感受有如瀕死狀態,故似恐慌。
初診時,醫師告訴我:「普遍認定,恐慌症是長時間處在焦慮狀態的結果,至於恐慌發作的感受,我們可以稱為焦慮狀態的最大值。而『長時間』的定義因人而異,可以追溯到很多年以前,也可以是短短的近幾個月。」
「所以妳最近有什麼心事嗎?或者和人吵架?」葉醫師向我解釋完何謂「恐慌」後,顏容慈祥地問。
「沒有,我幾乎不和人吵架,但會慣性失眠。」
「這樣啊,那表示妳潛意識裡頭太緊繃了。而且妳應該有存在許久的焦慮的事,只是妳自己不覺得,因為內化了。沒關係,這很正常,大家都是這樣。」葉醫師笑笑地,繼續說著:「妳不用擔心這個病會帶來多大的困擾,很多恐慌症的人,還是可以跟正常人一樣過生活,根本看不出差異,只是需要吃藥。當然,除了吃藥之外,還得配合作息和運動。」
「我要吃一輩子的藥嗎?」我問。
「不一定,每個人走到痊癒所花費的時間不同,跟妳自己的先天體質和後天努力有關。但別想那麼多,現在首要的,是要相信自己的身體、給自己信心,就不會當一輩子的藥罐子。」
「好。」我一直很鎮定,鎮定得異常。
「嗯?看起來不錯嘛,那就好。要記得發作的時候,別一直想著自己快死掉了,雖然那感覺很像、很逼真,但要相信,那死不了的。你不會死掉。全世界——沒有人因為恐慌症,而出什麼大事喔。」醫師口吻篤定,像是要給我灌輸自信。
「好的。」
我知道,我明白。正因為死不了,所以我可以持續且鮮明地感受到那樣的痛苦。
走出醫院,我突然覺得整個世界都不一樣了。這不是我的世界,我孤立而無援。
實際上,在拿到人生第一份精神科藥袋,開始服用抗憂鬱藥物的初期,我的情緒更為緊繃。首遇恐慌發作的那個夜晚,著實令我驚魂未定,光是想像一秒,我就害怕一切再重演。因而我排斥黑夜(超過晚上十點就會恐懼),排斥所有與發作時雷同的場景和感覺,例如日常的腹痛也令我困擾。那時,我總是早早就關燈上床,明明睡意未濃,藥效也尚未運作,我就想逼自己睡著。我越睡越多、越睡越多,也根本不想出門。我擔心自己若在外發作了,一瞬間氣力耗盡、狼狽、虛弱的模樣,會嚇到四周的人。
我不想被人看見那個模樣,以及解釋「我隨時可能變成怪物,但不久又會變回人類,如果遇到的話請不用害怕」——這類的話。所以後來縱然適應了藥物帶來的暈眩感,也讓病情從無依無靠轉善為偶爾平穩,讓我能照以往和朋友聚餐,並像個正常人一樣念書考試、畢業工作,我還是可以在夜深人靜時覺察,自己的雙肩從沒鬆懈過。內心永遠膽顫,雖然一再地努力克服,努力進行或深或淺的催眠,藥物對我而言近乎仍是唯一解。
當我禁不住跨次元地去到另一個空間苦痛、瘋癲時,我必須承認自己沒有任何朋友。我無法有任何朋友。這種寂寞,某程度來說,可以是最難捱且無法消除的副作用。是的,苦難伴隨苦難,苦難所引發的最大副作用,依舊是苦難。
然而,正因如是苦難,令我想起深夜的星星之火,我慢慢意識到,這片罕有人過問、卻多人到訪過的境地,其實一直存在著某股力量。我們這一群在苦難中掙扎的人,也許就是指引的火苗。雖然帶著病,且總是猶疑於生死之間而不為人接近,但會有那麼一天吧,這份暸解將傳遞而開。像星星,像火焰。像死亡的光,仍有能力帶給活著的人希望。
讓人相信,活著是貢獻,不活則是奉獻。而貢獻或奉獻,對世界來講都是好的。真的。一直到今天,我還是會這麼想,且一點也不覺傷悲。
「星星可以照亮絕望的深處,儘管星星本身是一團燃得孤獨的火焰。」
否則現在,我又為什麼寫下這些呢?
(本文節錄自《這裡沒有光》一書)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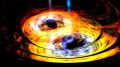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