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設想一個所有秩序都被破壞的世界,那裡沒有權威、沒有法律、更沒有制裁。在城市廢墟中,衣不蔽體的流民艱難地搜尋食物,為一塊手錶乃至一雙靴子大打出手;每個夜晚都有婦女會遭到強暴;街坊鄰居反目成仇;「不適當的」姓氏或口音同樣意味著殺身之禍……。
一切聽起來猶如夢魘,而事實上,這正是歐洲在二戰結束後一段時間裏的真實情況。在《野蠻大陸:劫後餘生的歐洲》中,英國歷史學家基思·羅威寫道,對數千萬人來說,歐戰勝利日並非噩夢的結束,而是他們的家園陷入原始蠻荒狀態的開端。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當痛苦而漫長的戰爭終於告一段落,用「支離破碎」來形容歐洲人肉體和心靈的狀態實不為過。身為始作俑者,德國付出的代價最為高昂:約2000萬人無家可歸,同時還有1700萬難民;柏林的一半房舍淪為瓦礫,科隆70%是殘垣斷壁。
並非每個德國人都支持希特勒,隨著同盟國特別是蘇軍的滾滾鐵流而來的,卻是針對全體德國人的無差別報復。尼莫斯多夫村是最先被蘇軍攻佔的德國領土,所有老人、女性和孩子都被殘忍殺害;在柯尼斯堡市郊區,遭到凌辱的女屍「或是散落在路上,或是被釘在當地教堂的十字架上,德軍士兵的屍體則掛在近旁」。
許多俄羅斯歷史學家堅決否認這些暴行,但無數親歷者和家屬的痛苦永遠抹殺不掉——在德國的城鎮和村莊,數萬名婦女在征服者的縱欲中死亡。家住柏林的一名女子回憶說:「被23名士兵輪姦後,我才敢去治療。從此,我再也不想與男人有任何瓜葛。」
有人會說,法西斯軍隊曾在入侵蘇聯期間犯下駭人聽聞的暴行,所以德國人罪有應得。即便如此,羅威在書中提供的大量細節,讀來依然叫人不寒而慄。
強姦,這是人類文明所不齒的最醜惡和野蠻的行徑。因為它無視人類自身的尊嚴和價值,因為它以強凌弱摧殘生命,更因為它的受害者是生養人類的女性。由於這些原因,文明社會對強姦行為的懲罰從來就是嚴厲的。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史卷中卻有著一段沒有受到過追究的規模浩大的軍人群體強姦罪記錄,那就是蘇軍在征服納粹德國後的大規模性放縱行為。由於這些犯罪者屬於反擊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屬於世界公敵的一方,這一駭人聽聞的集體罪行不但沒有受到過懲罰,甚至沒有引起國際社會的真正關注和譴責。惟一對人類歷史上的這場規模空前的強姦浪潮有刻骨銘心記憶的,就是那一批被蹂躪過的德國婦女。
那些從納粹殘酷統治下解放的國家,同樣無法在復仇狂潮中倖免。在義大利北部,約兩萬人被同胞殘殺;在法國的小鎮廣場,同德國士兵相好的婦女被剝去衣服、剃了光頭,暴徒在旁邊哈哈大笑;在布拉格,德軍俘虜被澆上汽油點燃;在波蘭監獄,德國囚犯頭朝下被溺斃在糞便中,還有的被迫吞下活蟾蜍而窒息死亡。
在納粹曾經濫殺無辜之地,復仇本能統治一切,似乎是無可避免的悲哀現實。猶太人也不例外。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解放後,黨衛軍看守被曾經的囚犯活活打死。「我們都參與了,感覺酷斃了。惟一難過的是報復得太少。」談到自己的暴行,猶太囚犯貢塔爾茲沒有絲毫悔意。而在達豪集中營,大兵讓幾十名德國獄卒排好隊,用機槍草草射殺。
彼時,絕大多數人相信,這一幕幕血腥的場景只是對昔日罪行的合理懲罰。因為不想失去公眾支持,同盟國領導人明知真相,依然對此聽之任之,連口頭譴責都少得可憐。正如捷克前總統薩波托斯基曾經不屑一顧地打比方說,「你砍木頭時,總會有碎片亂飛的。」
在基思·羅威看來,某種程度上,越往東走,當地人的所作所為就越遠離文明。在東歐各國,已平靜生活幾個世紀的德裔居民大批背井離鄉,這是他們為希特勒倒臺付出的、無法再大的代價。據不完全統計,戰爭結束後幾個月內,約有700萬德國人被趕出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驅逐了300萬人,其他中歐國家驅逐了約200萬人。無論怎樣看,這都屬於種族清洗範疇。不過在當時,波蘭和捷克都認為,「驅逐」是避免另一場戰爭的、最仁慈的方式。
事實上,種族暴力並非單純針對德裔居民。各國民粹分子的終極目的是「保持國家的同質性,洗刷掉異族帶來的最後污點」。1947年,波蘭當局實施旨在圍捕境內烏克蘭裔人士的「維斯瓦河行動」,將他們驅逐到偏僻的西部,令許多在戰時未受徹底破壞的村鎮十室九空。「這是種族戰爭的最後一幕,」羅威寫道, 「始於希特勒,由斯大林繼續,在波蘭結束。」
最接近黑色幽默的是,東歐諸國剛擺脫希特勒的魔掌,旋即又成為莫斯科的附庸。儘管精疲力盡的西歐無力再和蘇聯打一場「熱戰」,鐵幕的另一側,不是所有人都對新秩序表示服從。在波羅的海三國,拉脫維亞的「森林兄弟」游擊隊一度同蘇軍展開巷戰,謀求獨立未果;遲至1965年,立陶宛民族主義分子仍不時與蘇聯警方爆發槍戰;當最後的愛沙尼亞抵抗戰士,時年69歲的奧古斯特·薩比被擊斃時,二戰的火焰已熄滅了33年之久。如
果說二戰是歐洲乃至人類近代史上最黑暗的篇章,那麼,戰爭結束後濫觴於各國的復仇狂潮,則部分說明瞭這種黑暗的根源——以地域和血緣區分敵友的思想,其實一直潛伏在普通人靈魂的角落。正如基思·羅威在《野蠻大陸》中的總結:經歷了將近70年的道德含糊,是時候反思這場戰爭的結束方式了;何況,又有誰能保證歷史絕不會重複呢?
在柏林,很多見證者根據身邊發生的事件認為,從4月24日(紅軍攻入柏林市區)到5月5日(德軍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強姦的婦女達到 1/3,柏林的歷史學家桑德斯和焦爾根據多方調查得出一組謹慎的數字:10萬柏林婦女被蘇軍強姦,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強姦,近1萬人被強姦致死。在戰後劃歸波蘭的原東部地區,被強姦者達200萬,其中24萬致死。這裡面還尚未包括西普魯士地區、蘇臺德地區、東南歐的德意志族居住區和奧地利地區的受害人數。
很顯然,讓她們再去相信這個世界還存在正義和公理很難很難。當年,她們失去了做人的尊嚴,剩下的惟一價值就是在槍口的威脅下聽由勝利者泄欲。如此的遭遇她們寧願忘記。
眾多由德國人寫下的追述「二戰」的文字資料中,只發現了一篇由強姦受害人自己寫下的受害回憶。老人名叫希爾德伽特·克利斯托夫,在她 1997年去世後,她的女兒把母親生前口述的一些情況在一本名為《每天都是戰爭》的文集上發表了。老太太在戰前曾住在西普魯士的小城遜朗克,戰後被驅趕到巴伐利亞州定居。下面是老人的回憶摘要:
1944年末的冬天艱苦異常。東線的戰場一天天接近我們。我們的丈夫、父親、兄弟、兒子全在前線。我們從來沒有想過1945年的1月會有什麼樣的命運降臨。1月27日,是前德國威廉皇帝的生日,就在這一天,俄國人的坦克開進了我們的小城遜朗克。俄國人穿得非常厚實,長軍裝,大皮靴。他們衝進民房,搶走首飾和手錶。任何反抗都是徒勞的。遇到反抗,他們就開槍。第一夜,我們幾家鄰居集中到雷曼啤酒作坊,藏在頂樓上相互壯膽。我的表妹從柏林躲避轟炸住在我家,她帶著一個2歲的孩子。她有一支手槍,但子彈很少,還不夠我們大家自殺用的。我們在閣樓一夜未眠,聽到城裡到處都是槍聲。天亮後大家才敢回到自己的家。俄國士兵到處尋找年輕的女人,只要抓住一個,立刻拖到空房子裡,接著就輪姦。那時我24歲,每天提心吊膽的。
紅軍掌管了全城的秩序,前6個星期裡基本不允許我們出門。一天晚上,俄國人闖進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這一點太容易做到了,因為他們禁止所有的居民鎖房門。他們用槍逼著我們進入一幢空房。那裡站著一些年輕的女人。接著,集體強姦開始了,這些野獸撲向我們,一次又一次,持續了整整一個夜晚,直到天開始發亮時才離去。當我們拖著軟弱的身子回到家裡時,母親居然非常高興,因為她看見我們還活著。當時有很多女人被強姦後就被擊斃了。我們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殺,我們常常要去剪斷繩索,埋葬她們。
儘管這座城市有60%的面積是廢墟,但還有一些麵包房可以使用。俄國人把女人們帶去烤麵包。我們每天可以得到200克麵包。有一天,這些惡棍又把我們帶到了一幢空房子裡,讓我們給他們殺雞拔毛。全部工作結束後,我們不但得不到一塊雞肉,反而遭受了新的一輪強姦!後來我們被送到城外的一座農場去勞動。在那裡餵牲畜、擠牛奶、做黃油,給俄國人提供食品。俄國人來取食品時,常常要拉我進空房子。每到這時,我的母親都要擋住俄國人,苦苦解釋我懷孕……
阿諾特·尼登楚博士戰時在羅塞爾的一家醫院裡工作,他以一個內科醫生的身份見證了蘇軍的強姦狂潮。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俄國人攻佔東普魯士時,我作為約瑟夫醫院的主治醫師留在了羅塞爾。1945年1月8日,羅塞爾市在經過很微弱的抵抗後被蘇軍佔領,隨即開始了佔領者在城內的大規模毆打、焚燒、強姦和殺人。第一天就有60個居民被殺,其中多數是拒絕被強姦的婦女、試圖保護婦女和兒童的男子,以及不願意向俄國人獻出手錶和烈性酒的人。我的醫院有一天收下一個肺部被子彈打成重傷的流產孕婦。在一個俄國人意欲對她施暴時,她表示自己是孕婦,那個俄國人大怒,用腳狠踢她的肚子,並對她打了一槍。
強姦很快成為失控的風潮。根據我在醫院的瞭解,我相信在15歲到50歲之間的婦女中能逃避被姦淫厄運的只有10%左右。俄國人對他們的施暴對象幾乎不加選擇,被強姦者包括80歲的老人、10歲的小孩、臨產孕婦和產婦。晚上,俄國人從門、窗或屋頂進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尋女人,有時甚至在白天就扑向她們。他們大多帶槍,經常把手槍塞進女人的嘴裡逼迫她們就範。而且常常是幾個人按住一個女人,然後輪換著實施姦淫,結束時把受害者殺掉滅口。有兩個我認識的婦女就是這樣被殺的。俄國人還常常一邊強姦一邊毆打受害人。
我相信,只有很少的俄國人沒有參與這些可怕的罪行。在這方面,軍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別。當一個遭到強姦的10歲女童因下體嚴重受傷被送到醫院時,我實在按捺不住了,我通過波蘭翻譯責問醫院的蘇軍負責人:究竟有沒有可能制止這種行為?!對方答道:「最開始被允許了,現在禁止它就很困難。」當時也發生過把個別罪犯押送到蘇軍指揮部的事情,但這些人被關押幾個小時後就放掉了。
被強暴者發生性病的情況越來越多,特別是年紀小的受害者。治療的醫藥奇缺,藥房都被俄國人搶空了。醫院裡每天要做25例以上的性病處理。很多女孩開始嘗試和一個施暴者把性關係固定下來藉以保護自己。
蘇聯軍隊在征服納粹德國的過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這個詞,而戰後的德國人則習慣把納粹德國滅亡的時刻稱作「零點」,意指德國新的歷史由此開始。讓德國民眾接受被俄國人「解放」的觀念是很困難的。至少對於無數德國婦女來說,俄國人的到來無異於天塌地陷般的災難。男人被囚,女人遭姦,一個民族末日的最淒慘景象莫過於此。
哥廷根的歷史研究會曾撰文指出:在柏林,很多見證者根據身邊發生的事件認為,從4月24日(紅軍攻入柏林市區)到5月5日(德軍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強姦的婦女達到1/3,柏林的歷史學家桑德斯和焦爾根據多方調查得出一組謹慎的數字:10萬柏林婦女被蘇軍強姦,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強姦,近1萬人被強姦致死。在戰後劃歸波蘭的原東部地區,被強姦者達200萬,其中24萬致死。這裡面還尚未包括西普魯士地區、蘇臺德地區、東南歐的德意志族居住區和奧地利地區的受害人數。
在世界戰爭史上,軍隊對戰敗一方的婦女施暴的情況屢見不鮮,但罪行最為嚴重者則首推「二戰」中的蘇軍和日軍。那麼德國軍隊在這方面的記錄又如何呢?戰後,全世界包括德國本身對納粹德國的罪行做了深刻和廣泛的揭露,但大規模的軍隊強姦行為從未涉及。
哥廷根歷史研究會指出:「強姦風潮在德國軍隊中從未發生過。少量個案受到了德國軍事法庭的處罰。」史料表明,德國軍隊從普魯士時代起素有以侮辱婦女為恥的觀念。到了第三帝國時期,除了傳統觀念的影響以外,納粹禁止軍人的強姦行為還有另外兩層考慮,其一是要杜絕軍隊因此產生性病,導致戰鬥力下降;其二是防止「優良」的雅利安血統和其他血統的混合,導致種族異化。據納粹德國1943年12月14日的官方數字,黨衛軍系統設有固定法院31個,隨軍隊行動的師、旅級法院20個,軍團級法院5個,共有法官204人。在國防軍方面,1942年10月2日專門成立了一個編號為999的「緩期執行師」,這個師由兩部分軍人組成:違紀的軍人和看押他們的軍人,最多時關押了3萬名有損「軍隊榮譽」的軍人。以上軍隊執法單位的主要功能是監督和處罰違令、違紀和戰場脫逃,其中檢查違紀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是否存在強姦行為。
「二戰」中親身受過蘇軍性侵犯的勞申貝克女士在她1993年發表的《從皮卡棱到沙德林斯克》一書中也提到了這一點,她說:「德國軍隊在蘇聯的鄉村 (特別是烏克蘭)犯下的大量罪行無可置疑,但強姦行為是要受懲罰的。為解決德國軍人的性飢渴問題,國防軍設立了大約500個隨軍妓院。」這一點柏林的羅迪老先生提到過。他說:「我從來沒有聽說士兵強姦俄羅斯女人的事,這是嚴格禁止的。那麼軍隊裡的小夥子們的性慾怎麼解決呢?大家都去妓院,但我沒有興趣。」
2001年,女歷史學家蒂爾斯在採訪了30名遭受過蘇軍蹂躪的德國婦女後寫了一本書,名為《另一個世界的述說》。書中寫道:強姦大多數發生在黑夜,受害者很難辨認和事後指認施暴者。這樣就造成了婦女的整體恐慌。蘇軍的坦克部隊通常是連續推進的。在同一個地點連續住幾天的主要是步兵。大多數強姦就發生在這個時候。
蘇軍中有一些年長的士兵較少參與強姦,有時還像保護自己的孩子一樣阻止自己人對德國女孩子下手。即使存在上司的默許,也不是說每一個紅軍士兵都是強姦犯。面對面的強姦和謀殺他人是需要克服一種強烈的犯罪感的,這對一些單純的青年人來說絕非輕而易舉之事。所以,集體強姦比較盛行,因為參與犯罪的人越多,士兵個人的犯罪感和顧慮就越微弱。今天,當一些犯過此類罪行的蘇軍老兵談起這種事時,口氣就像談論一個週末下午的散步。他們並不認為50多年的那些受害者現在還會有什麼痛苦和恥辱感,他們認為那是戰爭情況下的非常時期的事件,而戰爭有其自身的規則。
是否該永遠沉默?對這個問題,受害者的態度表現出驚人的一致。她們說:「我們無法談起這些,永遠不能。」很多受害人當時還是十三四歲的孩子,她們不理解發生在她們身上的事到底意味著什麼,她們遠不如今天的孩子那樣生理早熟並擁有對性知識的瞭解。這種恐怖的經歷對孩子來說異常殘酷,並經常會導致精神或心理上的障礙。一些受害人對我說,她們成年後在性生活方面遇到很大困難。她們的情人和愛人只有在具備充分理解和忍耐力的情況下才能期待一個正常的婚姻。另一方面,因強姦導致的性器官的損傷和疾病還導致很多受害人患不育症和頻繁流產。……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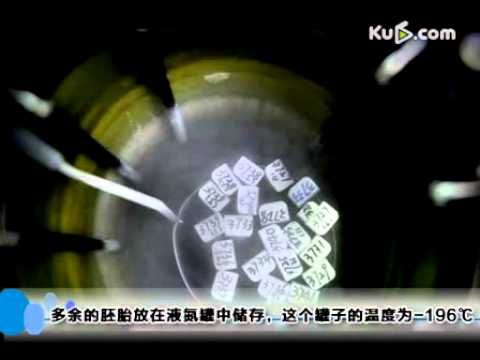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