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苏民讲述谭松记录
讲述人:魏苏民(1934年生)
采访时间:2005年元月30日
采访地点:重庆万州南通宾馆
记录整理:谭松
魏廉周之死
我是云阳县南溪镇青山乡人(1949年前叫二台乡),我父亲魏廉周在当地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家里有几十亩田土,是我父亲从我爷爷那里继承下来的。爷爷我没印象了,只知道人们叫他魏三爷,我见过他一张照片,穿着清朝的官服,我想他在清朝当过官。在我爸爸几兄弟中,我爸爸最能干,又有文化,到“解放”时(指1949年共产党夺得政权),家里除了田地,还开得有酒厂、盐厂(熬盐)和磨面作坊。爸爸有个侄子,叫魏炳全(音),他早年加入了共产党,快“解放”时,他劝我爸爸要认清形势,不要死守那份财产等等。其实我爸爸很看得开,钱财身外之物,要拿去就拿去。所以共产党一来,爸爸主动把所有田土家产统统上缴。上缴时怕路上不安全,还把金银财宝捆在我的身上,走几十里路送到云安镇去。爸爸缴得彻底呀,连他嫁出去的女儿陪嫁的金首饰都追回来缴给了政府,同时还积极为新政权征粮。另外,他还动员他的大哥(也是一个地主)把所有的财产交出来。由于爸爸缴得主动、积极、彻底,共产党把他评为开明地主,还让他到县城开“先进”会,我就亲自陪他去过两次。所以,从1949年10月云阳“解放”到1950年秋,爸爸人还算平安。
1950年秋后,上面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到南溪,我记得带队的姓冯。他们突然把爸爸抓来关起,关了一个多月,给他安了三条罪名:一、砍伐树林;二、转移财产;三、欠一条人命。这三条罪名都是不实之辞。首先,家里的田土、山林都作为果实分给了农民,农民去砍树与我家无关;第二,我们把家里磨面的机器搬到云安镇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搬的,当时共产党主要搞土改,对工商业还是保护,并没有说要收缴机器。如果当时要,拿去就是了,不存在转移。最后一条最可笑!在批斗会上,他们动员了一个农民上来控诉我爸爸逼死他老婆。为什么可笑?因为乡里大家都清楚,那个女人是因为家里吵架闹矛盾,一时想不开,寻了短。农民还是朴实,逼他当众说谎相当困难,当着我爸爸的面,他在批斗会上很狼狈,结结巴巴话都说不清楚。但是,他们还是把我爸爸杀了,用枪打的头。
我当时很想不通,财产全部缴了,总该免灾吧,但还是要杀!不过后来我想通了:如果他们想通过杀人来镇住其他人,不杀我爸爸杀谁?我爸爸在当地是最有影响的地主兼工商业主呀。
收我爸爸尸的是一家姓裴(彭)的农民,收得很仔细,把打出来的脑浆都捧起来入了棺。(陈沅森在《谈谈“土改”“杀地主”》一文中写道:“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大参考》2005.03.17)
其实当时农民和地主并没有深仇大恨,并不是像所宣传的那样。比如我大伯,他对佃户非常好,哪一家夫妻吵架,他都请到家来,招待吃一顿饭,好言好语相劝,所以后来工作组发动农民斗他,总斗不起来。最后他们找些不懂事的年轻人把他压倒,跪在地上,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主动跑上去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如此反复好几次。在斗完回家的路上,我大伯自嘲地说:我都六十多岁的人了,今天还拜了堂(注:旧时结婚时要跪拜三次)。
我爸的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修学校搬迁过一次,后来修公路被压在了公路下,再看不见了。
魏律民夫妇之死
爸爸死后,农协(农民协会)和工作组的人把我们全家赶到我家大院后面的旧房子里,农协的人则占据了大院的新房。这本无所谓,要命的是他们把我们所有的被盖都收缴了,紧接着就是冬天。我们一家十几个人怎么过?救我们命的是一个叫袁培君的农协会员,他看上我的一个妹妹,晚上悄悄从唯一的窗口塞了几床棉絮。如果不是这般“爱情”,我们活不过那个冬天。
后来他们认为旧屋也要收缴,又把我们赶出来,驱到山上,我们无家可归,在山上住岩洞。实在活不下去了!我年轻,无家无室,于是独自离家出走到奉节县当了个小学教师,后来又被调到一个剧团。
我说说留在乡下的我的大哥魏律民夫妇的事。
我共有兄弟姐妹11人,其中兄弟5人,除我以外,4个哥哥全部读了大学。大哥毕业于黄埔军校,因为婚姻回到乡下。新婚期间,蚊帐上的铁丝刺伤了他的眼睛,他因此留在乡下照看田产,没有再外出。“解放”时,我把他的中山剑等黄埔军校的东西统统沉到河里,怕惹祸。
“解放”后,他在乡下的日子很难过,实在过不去时,就走路到奉节来找我要点钱。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56年,他又来奉节,我给他30元钱,我当时月工资28元,还借了2元。我对他说,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你把大儿(魏京宇)送出来,在奉节找个事做,减轻一点家里的压力。于是,魏京宇来到了奉节。(魏京宇后来成了三峡地区有名的文物专家,2003年笔者为出版三峡专刊曾在奉节采访过他。)
1958年到1959年大哥被叫到山上去砍树炼铁,劳动强度很大。他是地主子女,更得拼命干,又吃不饱。1959年,他实在活不下去了,外逃到云安镇。逃走前,他偷了一件雨衣。在云安镇时,他去卖雨衣讨个饭吃,人家看他戴个眼镜,举止斯文不该像个落难的。追问他,大哥毕竟是个读书人,人家一追问,自个儿就慌了神。人们把他扭到派出所。在派出所,大哥一一招认了。你想,地主出身,又偷了雨衣,就这样,他被送进监牢,不久就死在里面。
再说我大嫂。1960年,她在乡下活不下去,走到奉节来找儿子魏京宇。当时我已调到了剧团,外出演出去了,没见到她。大嫂在奉节,把亲戚给她的几件衣服和一点钱全部留给了儿子,然后独自沿着梅溪河往上走。在这个时候她已经万念俱灰了。她跳进了梅溪河……
朱化成(音)之死
朱化成是我姐夫,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修养的人。他“解放”前担任了云阳县江口乡(现江口镇)的乡长。虽然是个小小的乡长,但是他竭力造福百姓,在当地口碑很好。“解放”后,凡当过旧政权乡长的都要杀。我姐夫也被抓起来,前后陪了两次杀场。那时一杀就是十多个,二十多个。比如,杀县长张之甫(音)那次就杀了21个人。为什么没杀他?说来你不信,当地几百农民(包括镇街上的人)联名上书保他,为他求情。在这种情况下,姐夫逃过一劫。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姐夫被抓进了劳改队。
我姐夫练过功,身体很好,在劳改队他拼命劳动,多次被评为积极分子。但是,他的身体因此拖垮了。大约在(19)70年,姐夫死在劳改队。
采访后记
偶然听一个朋友说起,她的一个朋友的祖辈,在土改时被枪杀了,我便请她帮我联系,说我想去找她聊聊。她的朋友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从重庆赶到万州,在宾馆里先同她沟通之后,再请出了她父亲魏苏民。
我们边吃边聊,老先生盯着我直截了当地问:为什么要来了解土改和地主的事?我支支吾吾地说,我打算写一部关于三峡地区的小说,想收集一些素材。我既不便笔录,更不敢录音,只得以摆“龙门阵”(聊天)的方式了解那一段往事。遇到关键的人名地名时,便借上卫生间赶快记在小本子上。
外面,江水正一步步逼来,把一段段历史永沉水底……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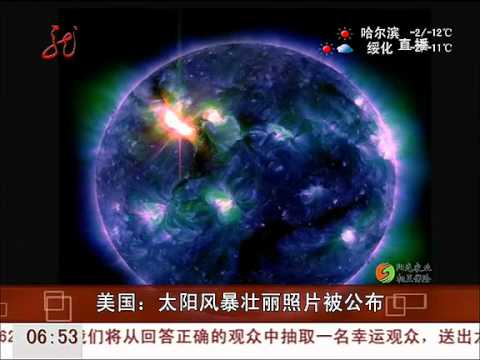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