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兰2010年4月14日出狱
倪玉兰这两月
何杨在拍完倪玉兰的纪录片后发现,“很多恐惧其实是多余的”
编者按:通过朋友介绍,何杨从5月上旬起开始跟拍倪玉兰,那时候她就像一个被遗忘的死角,“她是西城的,东城的警察大概也不愿意惹麻烦吧。”
他拍了10天,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惨烈的故事,但是倪玉兰让他感到意外。“遭受了这样的苦难,大多数人都会变得激愤、偏执,甚至自暴自弃,但是倪玉兰仍然这么平和,她似乎有消化苦难的能力,或者说,她是站在苦难之上的。”
警察对倪玉兰说:“你别在网上骂我们!好话也别说。”
一
4月14日 星期三 晴
9点30分,我被叫出监舍到谈话室接受了最后的检查,他们把我的双拐拆卸分离,将我放在里面的十二张申诉书和我惨遭虐待的图片搜出不让带出。我身上穿的衣服包括内衣内裤和袜子全部被脱掉接受严格的检查,直到她们认为确实没有东西藏在衣服里面才让我穿上衣服。经过40分钟的折腾,他们才将我送出大门。老伴女儿和好朋友来接我,他们跑过来和我拥抱……终于和亲人团聚了。
律师倪玉兰这一天出狱。当晚,她在一家小旅馆洗了一年多来第一个热水澡。2008年12月18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她有期徒刑两年,刑期从被羁押的 2008年4月15日算起。
那一天,按照倪玉兰的说法,西城公安分局新街口派出所纠集一群人,没有任何手续,闯入她家强拆,倪玉兰架着双拐与他们理论,结果被警察拖入警车踢打,后又被抓进派出所。
公检方的版本则是,倪玉兰暴力阻碍工人施工,致使尤德林、李鸿桥受轻微伤,被民警传唤至新街口派出所接受调查,当日11时许,在新街口派出所第三谈话室内,倪玉兰不服从民警管理,踢打民警肖巍下体,致使其睾丸挫伤,被当场抓获。
北京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接处警记录显示,在倪家所在的前章胡同19号,“我所民警及巡逻车均在现场,无打人现象”。倪玉兰的丈夫董继勤据此认为,说倪“殴打他人”是诬陷。
在独立导演何杨的纪录片《应急避难场所》里,倪玉兰对着镜头说:“到了派出所以后,他们把我关进小黑屋,先让保安揍了我一顿,一会谁进来就踢我一脚,踹我一脚,把我从地上扔到沙发,又从沙发扔到角落里。我要求上厕所,他们就让我爬着去,不然就是违反派出所的管理规定。”
二
倪玉兰住了一天就搬出来了,120块一晚太贵。他们找到另一家小旅馆,公共卫生间,50元/天,房间大概有6平米。
4月17日 星期六 阴
今天是我获释的第四天。前两天片警找老董说,监狱已将我释放的信函发送到了西城区政府部门,至今他们没有对我的居住和生活有任何说法。
他们早就无家可归了。2008年11月,倪家的房子被彻底铲平,现在,那里立着围墙和塔吊。这些天,来访的多是一些老朋友,说得更明确些,是老访友。
1986 年,倪玉兰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在中央某单位,同时在正义律师事务所兼职。1994年,她又被安排到中国国际贸易总公司做法律顾问。从2001 年开始,倪玉兰代理了一些敏感的案子。“(案子)谁都不敢碰,受害者找到我父亲,他是解放前的老律师,他说,我支不动别人,还支不动我女儿吗?父亲的话,我能不听吗?”她说。
于是家里其他亲戚给她打电话,别跟政府作对。大家都害怕和她联系,不然就会被“调查”。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2002年,这个城市已经“拆”出了一个自我维权的群体。这一年的4月27日,西城区新街口四条55号强制拆迁现场,很多拆迁户前去声援业主,倪玉兰举着相机也在其中。
后来她被指控对现场工作人员和民警施行暴力,以妨害公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倪玉兰则说,她的左腿就是那时被打得肌肉萎缩,从而再无法正常行走。
三
4月20日 星期二 阴
今天是我获释后的第七天。老朋友见面百感交集,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人们在探讨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正当维权依法反映问题,却要被判刑,被劳教,被拘留。有些人因长年上访得不到解决,将自己的感言写成对联,上联是天灾千方百计治理,下联是人祸千方百计遮盖。
22日起,事情变得有点奇怪。小旅馆的老板开始让他们反复换房,一会儿说这间屋子是服务员住的,隔天又说另一间屋子已经租出去了。26日,董继勤看见两个警察走进了传达室。
4月28日 星期三 晴,大风5-6级
今天是我获释的第十五天。我和老伴在旅馆小屋住了14天,从22号这天起我们就没安宁过。上午我们就搬离了。老伴顶着五六级的大风推着轮椅徒步走到市政府小花园。在这里我看到了两年未见面的老朋友张,她给我送来了被褥。下午我们到南河沿皇城根遗址公园避风。今天是我和老伴开始流浪生涯的第一天。
他们在路上捡到一个红色的编织袋,拉链有点坏了,但是还可以装东西。这样,他们的家当就增加到了一个、两个、三个编织袋。遗址公园里有半下沉的广场,那里风稍微小一点,也有太阳,他们就呆在里面。
这儿是应急避难场所,“我认为这就是救助一些生活没有着落的人的,”倪玉兰说,“而且这里离市政府近,要有个什么事儿交材料也方便。”
天慢慢黑了。一个保安指点他们,五四大街地下通道那里风更小一点。平日,那里总是有流浪汉呆坐、徘徊。他们在那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下午,“特别无助”的倪玉兰让老伴给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打电话,对方说正在开会,“你去找你们区政府吧。”
四
皇城根在北京的内城,有北京市民路过,问他们:你们是外地来北京看病的吗?倪玉兰对他们说:不是,我们是北京的,拆迁无家可归了。“赶上(拆迁)那个时候的人一听就明白了,”她说,“也有没赶上的,有人就问:北京还有这事儿?”
2002年,倪玉兰被吊销了律师执照。2003年出狱后,她腿脚不便,就在家里接待访民和维权者。 “我们是为了寻求一个真理,我们走法律途径,没有任何过错。”
她让他们熟记宪法第四十一条:“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她教他们写材料,告诉他们要简单明了,不要啰啰嗦嗦,“不然别人不爱听”,也不要写那些过激的话,有基本事实和证据就好了。
她还帮助他们联系媒体,安排他们接受记者采访。
5月2日 星期日 晴 31度
早晨勤带我去洗澡,换衣服。这两天天气变化太大,前几天还出奇的冷,这两天就热得难以忍受。
5月6日 星期四 晴
王买了草莓来看望我。晚上他们又给我送来了饭菜。郝买了鸡蛋煮熟后给我送来了。
5月8日 星期六 阴 大风
下午高老太给我买来了衣服和食物。衣服的颜色特好看,这是我两年多以来第一次穿这么好看的衣服。傍晚贝贝(倪的独女)来看我,得知夜晚有雨,就将所有的东西搬到地下通道。夜里下的雨相当大,多亏我们及时搬到这里避雨。今天白天的风比较大,不知道为什么患上感冒。
5月13日 星期四 晴
王和叶来看我。王给我炖了一碗羊蝎子,叶买了四瓶绿茶。
他们和她在一起。
五
通过朋友介绍,何杨从5月上旬起开始跟拍倪玉兰,那时候她就像一个被遗忘的死角,“她是西城的,东城的警察大概也不愿意惹麻烦吧。”
他拍了10天,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惨烈的故事,但是倪玉兰让他感到意外。“遭受了这样的苦难,大多数人都会变得激愤、偏执,甚至自暴自弃,但是倪玉兰仍然这么平和,她似乎有消化苦难的能力,或者说,她是站在苦难之上的。”
1960年出生的她说,从小受到的是关于崇拜的教育,“随着教育和经济的增长,我慢慢地对崇拜有了另一种看法,我改崇拜法律了。我什么时候都要跟他们讲理讲法,虽然你讲法,他说你跟政府作对,你讲理,他说你扰乱公共秩序。这两年,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刚强了。”
她第二次出狱的时候,还是带出了一样东西,他们没检查出来。那是写在卫生巾上的《认罪悔罪书》,第一句话是,“我是被称为罪犯的倪玉兰。”
在讲述到最痛苦的经历时,她的表情也没什么变化,好像在叙述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然而她却偷偷在公共厕所里哭泣——两年的牢狱生涯让她的表达能力直线下降,为了重新流利地说话,她朗读报纸,但总是不停地念错。灯光也成了可怕的东西,监舍永远是一排白晃晃的日光灯,现在,她在日光下能看见的字,在灯光下就看不清楚。
六
除了访友,还有别的“小人物”愿意伸出一只手来。一个小保安,准备辞职不干了,临走前去看倪玉兰,给她买了只大鸡腿。“外地街坊”买菜回来,就塞给她西红柿和咸鸭蛋,“我多买了点,给你带过来。”一个老头,住在胡同里,小心翼翼地问她:我们家烙的鸡蛋饼,吃不完了,你要吗?倪玉兰接过饭盒,饼码得整整齐齐,“我就知道是他专门去买给我的,怕我不肯要,才这么说。”
5月15日 星期六 晴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个人。一连几天都在那里鬼头鬼脑地探寻,我们给他拍了正面照。他抽的是大中华香烟,留下一堆烟蒂。2点到4点多钟一直都在那里。
短暂的不被打扰的日子结束了。
21日晚,睡得太熟,早晨起来,她发现雨伞不见了。隔了一天,她和老伴去附近东来顺的后面躲雨,回来发现老伴的自行车也不见了。
怕继续丢东西,他们决定轮流睡觉。倪玉兰觉得,这是有人故意让她生活得不方便,“他们就想让我们报案,一报案就可以借机把我们轰走了,我们就忍着不报。”
5月26日 星期三 晴
晚上8点多钟,来了两个警察。他们嘀咕一会儿就走了,不一会儿又回来直接向我们问:是倪大姐吗?我说是,你们是谁。他们说,我们是市局的。其中一个高个警察,自称姓王,给我们摄像,他们摄完像就要走。我说,再呆一会儿吧。另一个姓江的警察说,我别再招(惹)你们啦!
5月27日凌晨起,先是西城的警察把他们带回区内,中午送回。从这天起到6月4日,东城的警察和他们玩起了例行公事的猫鼠游戏:警察来一次,他们就得收一次帐篷,站到路边,待其离开。
5月30日 星期四
今天是我们流浪街头的第33天。几天没有睡觉了,感觉特无力。下午天气不太好,小雨由小变大,一阵接一阵地下个没完。晚上以为不会再下,谁知比下午厉害得多。早晨起来,帐篷四周的被子全部湿了,衣服也湿了。
七
何杨拍了10天,剪了7天,6月1日成片,6月5日传到网上。他开机两天,从自己的机器上监测到下载人数超过了两万,“后来种子散布出去,就没法统计了。”
6月6日 星期日 晴
早晨一位女网友给我送来一束鲜花,她走后不久又来了一位小网友,他只比贝贝大一岁,他在这里和我长时间地交谈。他很可爱,走时偷偷在报纸下给我放了200元钱,他走后我才发现。
6月10日 星期四 阴转晴
今天是我们流落街头的第44天。一位外地网友发来短信说:“倪律师,祝您身体早日康复,我有机会来北京的话一定来看您。”
下午有3位人民大学的学生来看望我,买了桃子、香蕉、西瓜、雨伞。晚上6点半多,网友小袁看望我,给我捐款,教我如何使用微博。
也有一个胖子,装成有过上访经历的网友来套话,被一位访民识破。“你别在我们面前说共产党的坏话,”倪玉兰告诉他,“我们还指着共产党给我们解决问题呢!”
八
网友第一次行动是15日。 14日晚11点,东华门派出所一警官强行将倪玉兰夫妇的包裹装车,并将人带入警局。倪通过短信和微博求助,8名网友赶来要人。15日凌晨4时,派出所放人。
随后部分微博用户发出消息,号召大家6月16日端午节晚上和倪玉兰共度佳节,品粽消夏。为了让倪玉兰能准时出席,他们甚至在15日打了一个掩护,让她突然“消失”一晚——实际上她被护送去了崇文区的一家宾馆。
16日将近晚上7点的时候,网友们在五四大街的地下通道见到了倪玉兰夫妇,大家正在握手寒暄时, “警察呼啦一下就下来了。”
他们对网友拍照、录像,“我们也对他们拍照、录像,互拍。”网友张大军说。2009年,他就曾与网友前往湖北大厦抗议邓玉娇事件,“我记得那一天也是端午节,来了10个人。而今年,只是发了个消息,就来了将近30个人。”
在口头传唤后,警察推着倪玉兰坐的轮椅开始往派出所跑,网友们步步尾随,而后在东华门派出所形成“围观”阵势。
倪玉兰人在派出所里,接受警察询问:“你上网吗?你发推特吗?”他们不让她用电话,“现在外面那么多人,待会儿你又给我弄好多人来!”
派出所外,网友们唱起了国际歌。接近晚上11点,张大军等网友在警察的“护送”下有序撤离,在空旷的王府井大街,响起了这样的口号:倪玉兰,回家!
倪玉兰次日凌晨1点被警方送回了西城,住进一家宾馆,临走时警察对她说:“你别在网上骂我们!好话也别说。”
回忆这一段时间,她惯常平静的神色不见了,开始笑起来。
张大军认为,最近一年兴起的这种新的抗议形式,不针对宏大事情,而是具体事件,把网络的众声喧哗变成了实际的行动,“我们围观警察,也被别人围观,这是对公民权利的申张。”
何杨原来拍的是人类学纪录片,拍完《应急避难场所》后,他发现“很多恐惧其实是多余的”,他说自己要继续放弃恐惧直面苦难,不过,“真正让我放下心来的正是倪玉兰的平静,如果她一天到晚害怕,我想我也会害怕的。”
- 关键字搜索:
- 女律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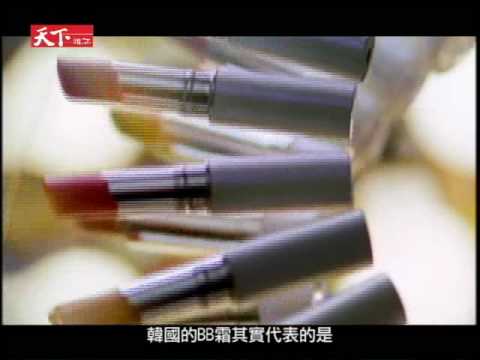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