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6月26日訊】一、反 右
我從部隊轉業,教了三年小學,一九五五年進入四川開縣中學當教師。
一九五七年初副校長唐巨星從成都開會回來,向全體教師傳達了「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後加以修改,公開發表時題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講話中指出「疾風暴雨式的大規模群眾階級鬥爭已基本結束」,提倡「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號召「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他說「馬克思主義也可以爭議」。我不由出自內心敬佩毛澤東的偉大,我感到「毛澤東真像一座高聳入雲光芒四射的燈塔,照亮了中國的前途,照亮了革命的道路。」
開中黨支部書記廖化堅兩次動員我給共產黨提意見。開縣縣委召開的座談會上,縣委書記王煜山說:「我以黨性擔保,絕不打擊報復。毛主席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難道連毛主席的話也不相信?」
開中鳴放座談會上,我就農業合作化不要強迫農民入社,就開中發展黨員要全面考察,開縣文教科官僚作風等問題,提了三條意見。七月中旬反右運動中我被劃為右派份子。批判我誣蔑合作化運動,挑撥黨群關係,反對共產黨。
十月處分下達,我被撤去教師職務降為勤務人員,發生活費20元。
一九五八年三月發放到邊遠山區岩水勞動改造,在農村勞動了五個月。九月,全民大煉鋼鐵,全縣在岩水區各鄉勞動的右派全部轉到白泉鄉蔡彎運輸鐵礦。從此,更大的苦難降臨到我們這些右派的頭上。白泉鄉是岩水最高最窮最偏遠的地方。距我們所在的麻柳大隊一百二十餘裡。接到通知大約上午九點,限定次日中午以前趕到蔡彎。麻柳大隊勞動的右派共有8人。徵調的還有全區各鄉農民。去蔡彎路上的人絡繹不絕。紛紛傳說蔡彎發現了大鐵礦,藏量十數億噸。下午太陽偏西的時候,路上已經行人稀少,民工都走在了前頭,麻柳的8個右派也都各自走散。我挑著一口小箱子和一個被蓋卷落在了後頭。飢餓疲倦的我拖著腳勉強前行。路邊做活的農民提醒我:「走快點,天一黑,過不了猴攀岩。」我努力加快腳步。
穿過一片樹林,突然眼前一空,面臨一座山谷,兩山相距三五百丈。岩下河水發出吼聲。日頭西斜,陽光照到的地方峭壁削立。下半山谷陰霧迷濛,看不到谷底。一條獨路,呈「之」字形,三五丈一個拐彎,一時向左,一時向右,曲折下行,坡度在45度以上。路寬二尺左右而且很不平整。前面有人陸續下走。挑著行李磕磕絆絆是不行的。我把木箱被蓋綁在一起,背在背上,將心一橫,向下走去。靠緊岩壁,抓住小樹、小草,扣住岩縫。一步一步慢慢走下。不敢看一眼懸空的一面。下行三五十丈,緊張的心情剛剛放鬆一點,突然從下面傳來「啊——」一聲驚叫,接著聽到「碰——!碰——碰!」連響數聲。立馬有人喊道:「摔死人了!摔死人了!」我心臟緊縮,頭皮發麻,一下坐在石梯上面。最後,我自己都不知道怎樣走到岩底的。到我淌著齊腰深湍急的河水走過河去時,天色已接近黃昏。
幾天之後才聽說摔下岩去被河水沖走的人,也是一個發放到岩水勞動的右派。據說姓趙,在縣聯社工作,又說是縣工會的人員。其他情況就一無所知了。
這是第一個死在岩水區的右派。
蔡彎運礦,最後是一場鬧劇。一下子集中幾千人去蔡彎挖礦運礦,首先是生活嚴重困難。這裡地廣人稀,沒有住處。幾戶人家,茅草房檐下都住滿了人。雖然搭了幾十個竹棚,仍然容納不了。好些民工住在岩洞之中。沒有糧食,缺乏鍋灶,每人每餐只能吃一碗半生不熟的紅苕。沒有開水,就在山溝捧水解渴。根本沒有道路,又加連日陰雨,凡能通人的地裡都踐踏成稀泥爛洞。通向外界的只有猴攀岩一條險陡的獨路,鐵礦運不出去,也無處儲藏,堆放在山谷當中。民工由四方調來,缺乏組織,一片混亂。勞動卻催促得緊,各個山頭站著監督哨崗,手持話筒不斷喝斥:「不准打站,不准偷懶!」雖才九月下旬,氣溫不斷下降,有時飄起雪花來。絕大多數民工沒有棉被,衣服破爛單薄,難以遮體。飢餓,寒冷,勞累,病倒不少的人,沒有醫生,沒有藥品,進入蔡彎不過半月開始死人。怨聲四起,部分民工,拒絕出工,幾個幹部無可奈何。聽說到撤出蔡彎時,不過一個月,死了六七個人。我知道的麻柳大隊一個姓謝的五十歲的老農就死在蔡彎。
我大病一場,高燒三天,倖免於死。
十月,下令撤出蔡彎,許多人因而能夠生還。原來挖出的鐵礦品質太差,無法煉鐵。不僅勞民傷財,好幾個農民搭上了生命。政府行為,為何這樣草率?
我轉移到岩水區所轄花梨鐵廠繼續勞動,轉去的右派共三十三人。花梨鐵廠廠址原先是一座廟宇,條件比蔡彎好,起碼有房屋可住。三十三個右派全部分到運輸車間。每月糧食供應四十五斤,基本可以吃飽。但管理非常嚴格。指定一個姓鄭的右派作為組長,每個右派分配了定額任務。運輸方式分兩種,推雞公車和肩挑。山路肩挑,挑到公路用雞公車推。我的定額每日280斤。兩種方式同時運用,先從山上把黑炭或礦石運到公路裝車,必須往返三次,三挑才能裝滿一車。三天一結賬,完不成任務受嚴厲處罰,扣飯,罰跪,挨打。
三座高爐日夜燃燒。全廠運輸工人三百多人。起先不很吃緊,不久糧食供應減少,45斤——40斤——35斤——28斤。肉食沒有,蔬菜沒有。每日往返少則七八十里,多則百餘里。大雨,小雨,打霜,降雪,不得稍停,節日假日,年關春節一律取消。民工開始逃走人數日益增多,有時出工的民工不過二三十人。廠方無計可施。三座高爐的燃燒礦石每日消耗四五萬斤。主要任務全部落在三十多個右派身上。
一九五九年,右派開始死人,而且連續不斷
第一個,陳克相,念過金陵大學,開縣初二中生物教師,平日不讀書,不看報,不問時事。批判「儲安平黨天下」右派言論時,他開會遲到,學習組長問他對「黨天下」有何看法,他連連點頭:「是黨天下,當然是黨天下,共產黨的天下。」因此反成右派。
一日大雪紛紛,道路泥濘,天色已晚,又累又餓,他把雞公車上的黑炭卸下二三十斤放在路邊,準備次日運回。被右派組長鄭XX舉報,立即被吊起拷打,兩隻手腕神經斷裂,生活無法自理,再被扣飯,命喪黃泉。
第二個,劉炎文,二十一歲,中專畢業分配來。過去身強力壯,進廠以後日漸消瘦,到一九五九年秋已十分衰弱,兩次結賬都未完成任務。又向農民買了幾斤糧食,被認為是消極怠工,破壞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鬥爭會上,遭扁擔亂砍,倒地哀嚎,再被扣飯,十多天後死在床上。
第三個,王小寒,成都人,父母是大學教師,中專畢業。一九五六年分來開縣農業局,一九五七年反成右派。高度近視,體態文弱,進廠以後積極勞動,受過表揚。一九五九年底已形銷骨立。一日,大雪漫天、寒風怒吼,一早出工,從此未歸。不知死在哪條小路,哪個山谷。死後,無人問過。年僅二十一歲。
華年嘉,蔡文淵、趙永秋、盛德俊……一個接著一個死去,好些倒死在路途之中。
我不願挨打受辱,拚死命勞動。一九五九年冬小便尿血,腰部劇痛,終於倒在路上。
一九五九年底在岩水區診所住院治療。所謂治療不過停止勞動,臥床休息。因為全診所只有一個醫生,一個農村姑娘充當護士。除了阿司匹林、頭痛粉之類,沒有其他藥品。病號每月只供應口糧12斤。12斤中搭配豌豆五六斤。油無一滴,蔬菜沒有。又病又餓,不是病死,也得餓死。
同病室三人都是花梨鐵廠勞動的右派。一個叫楊純,一個叫盛德俊。盛年近五十,原縣工商聯幹部。什麼病,怎樣反成右派,不清楚。我剛進診所他還能走動,逐漸不能起床,一九六〇年正月,一天早晨冰冷氣絕,不知死在何時。通知單位,沒有回音,家屬聯繫不上,第五天下午才草草掩埋。死後更加乾瘦,頭部像個骷髏,一雙赤腳伸在被外。盛德俊死後,楊純搬去與炊事員同住,我精神不濟,也無處可去。盛德俊與我床位相連,我成了他守屍的人。整日沒有人來,除了林濤呼嘯,聽不到聲音。相伴的只有盛德俊的一具屍體,與我抵足而眠五天四夜。第四天已開始發腫,併發散臭味。我仍無法逃避。我躺在床上,有時迷迷糊糊。很少思維活動,甚至不去思念親人。我既沒有了同情,也不害怕死人。彷彿成了一具尚有氣息的屍體。我想人到了這種境地就會麻木不仁。
我以為必定死在岩水,埋骨異鄉了。不料突然轉機到來,中央命令停止大煉鋼鐵,鐵廠還活著的十多個右派轉移到縣城附近白鶴公社紅旗大隊從事農業勞動。我得以絕處逢生。
二、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一年五月摘掉右派帽子,一九六一年底恢復工作。當時我除了穿的一身破舊的衣服,蚊帳鋪被,一樣俱無。添制鋪被沒有布票(一套鋪被要布票三丈以上,每人每年只發三尺),也沒購買的錢。到任何單位起碼必須鋪被一套。只得把我分到妻子所在的復興公社小學附近的一所初中。一九六二年調溫泉區中學,妻子調附近小學。
在溫中,我既是教師也是勤雜人員,上兩班語文課,還得兼管圖書,抄文件,常常打鐘搖鈴。工資32元,低於其他教師一半以上。但形勢逐步好轉,物資日漸豐富。可算平靜地過了四年。覺得生活有望,妻女一起,我感到滿足。
一九六六年上學期開始批判「燕山夜話」,批判「三家村」,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山雨欲來風滿樓,又將有一場大的政治運動。我擔心自己的命運,也為國家社會的前途擔憂。我又安慰自己,我謹言慎行,兢兢業業地工作,心想應當平安無事。
那個時候,決定命運的不是自己。一九六六年七月文化大革命一來,我又被打成黑幫分子,再次墮入苦難的深淵。
事出有因。在復興初中階段,一個姓陳的教師問到我在岩水區勞動右派死人及餓死農民的情況,我作了如實的回答。姓陳的教師教物理,一天集體勞動,休息時,他邀請我和另外一位教師到附近理化實驗室休息。實驗室裡有一架座式收音機。他打開收音機,調臺的時候,收到了臺灣廣播。雜音很大,只聽到了「……大陸的同胞們……」幾個字,發現是「敵臺」(當時蘇聯、美國、臺灣等廣播電臺統稱敵臺),立馬把收音機關了。
這是四年前的事,此後與姓陳的教師也毫無聯繫,這些事也已淡忘。不想文化大革命中陳老師被揭發批鬥,把我也牽扯進來。
大會鬥,小會批,一連四十多天。吃飯,睡覺,上廁所被四個紅衛兵押上押下。最殘酷的折磨是逼迫我睡在學生用的三層木床上的頂層,在相距不足三尺的天花板上安裝一盞40瓦的日光燈,通宵開燈,當時氣溫40度左右。日光燈灼熱地烘烤全身,強烈的白光刺激眼睛。哪裡還能睡覺,連呼吸也很困難。紅衛兵說這是「用毛澤東思想照亮反動分子丑惡的靈魂」。我只得用浸濕的毛巾被覆蓋全身勉強支撐。不到三個小時就被烘乾。紅衛兵輪番休息,我卻整夜煎熬。白天還得挨批鬥,寫交代,這是一種酷刑。我迅速消瘦,神智恍惚。一次批鬥會上一陣頭暈,兩眼發黑,失去了知覺。
先是全縣完中教師集中開縣中學進行文化大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九月返校繼續鬧革命。回到溫泉中學,對我繼續批鬥,監督勞動。
我妻子所在小學與溫泉中學相隔一個球場,已懷孕臨產,我再三要求仍然不准回家,不准見面,不准通信。
十月四日早上,小學通知我妻已生產,出血過多,情況不好,讓我立即回家。我向縣委工作組姓崔的組長請假,答覆是:「你又不是醫生,回家有什麼用!」我淚流滿面,反覆懇求,批准20分鐘。而且強調:「不能超過20分。」我被紅衛兵押著走進臥室,數月不見,一見之下妻一激動,立馬休克,雙目緊閉,不省人事。我手足失措,不知怎樣是好。接生員慌忙搶救。幾分鐘後未見甦醒,我痛哭失聲。紅衛兵宣布20分鐘已到。我哀求延長10分鐘,等候妻子甦醒,不由分說,兩個紅衛兵架著我的兩臂把我強拉出門。回頭張望,妻滿臉蒼白,仰臥床上,不知死活。此時,只有四個字可以形容:「心如刀割」。
第二天,七八個紅衛兵押解溫中四個黑幫去溫泉鎮挑米,返校途中經過小學,繞道幾步就是妻臥室的後牆。我趁機快步來到後牆窗下,撕開窗紙看見妻子躺在床上,孩子放在側旁。喊了一聲,妻剛答應,紅衛兵追來大聲呵斥,把我趕走。一句話都未說到,孩子是男是女都不知道。見妻還活著,便是最大安慰。
一九六七年我被發放去溫泉公社黃金大隊挑水庫,勞動強度大,舊病復發,腰痛劇烈,小便尿血。好在農民並不苛刻,雖然不准住院治療,但可適當休息。心境較為平靜。
一九六八年三月突然接到通知:「立馬回校,交代問題,接受批鬥」。這時工作組已經撤走,造反派掌權。回到學校,威脅逼迫,要我承認是地主階級分子。我一九三八年十三歲離開開縣,到外地讀書。一九四九年五月停學返開,從未經管過家事,如何成為地主?因我拒不承認,加大鬥爭火力,輪番上陣,日夜不停,鬥我一天兩晚。最後我才明白。造反派的根據是:在我檔案中查到一九四九年八月我曾為地下黨籌集經費稻穀一百擔。由此判定我是地主階級分子。我再被關押,強迫勞動。
一九三八年,我十三歲隨舅舅到閬中讀書。後離開舅舅到成都涪陵等地讀書。一九四九年我考入梁漱溟主辦的北碚勉仁國學專科學校。後轉入相輝院文史系。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參加重慶學生運動。一九四八年參加學生組織突兀學社。學社委託我主編小型刊物突兀日報,報導工人學生運動。一九四九年五月受國民黨重慶警備司令部追捕逃回開縣。六月與地下黨員祁七中(原重慶重華學院學生)發生聯繫,參加地下黨工作。八月祁七中受組織指派要我籌集經費。他告訴我有幾個地下黨員有暴露危險,必須盡快逃離開縣,需錢至急。祁七中還說如果允許,可以公開說是為共產黨籌款,解放後政府歸還。我城中鄉下日夜奔走,毫無門路。
我家原是開縣富戶,但父親早逝,母親哥哥吸食嗎啡,迅速敗落,已臨完全破產,債主盈門。我返開後住在叔父肖光祖家中。正無計可施的時候,聽說母親賣掉了最後一份田土,賣了一千多擔稻穀,剛剛成交。我知道母親日夜顛倒,愛在白日睡覺,起床很晚。我打算去試一下有否籌錢的可能。早上母親熟睡未醒,小皮箱並未上鎖。打開有谷條數十張(當時地主賣谷都是開出谷條,買主憑條到佃戶手中領谷,土地買賣都以谷條成交),我趁機抽出三張,共稻穀百擔,立即交付祁七中作為黨的經費。
這是母親最後一份土地,她欠債很多,追逼很緊,我卻偷走了百擔谷條,當時深感內疚。不料現在卻成了我的罪行與罪證。
「往亊微痕」供稿
「往亊微痕」更多故事請看﹕
//m.yzblive.com/taxonomy/17798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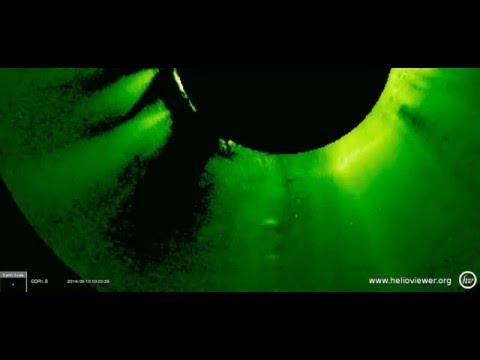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