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田達志孤寂的背景,他一直樂呵呵,很少露出對這片沙漠和種樹的焦慮
增田達志
「日本人增田達志在呼和浩特白二爺沙壩種下樹,樹活了,但中國迷失的社會慾望卻無法成全他的‘生態平衡’烏托邦。」
2012年4月的一個週末,一個來自北京的志願團隊抵達內蒙古和林格爾縣,日本人增田達志像主人一般迎候多時。
在過去15年裡,這個日本人像候鳥一樣往返於日本大阪和位於和林格爾的白二爺治沙基地之間,累計治理沙漠七千多畝。
「我喜歡沙漠,但不得不親手消滅它。」增田經常這麼闡釋自己的動機。不過,這位46歲的社會心理學博士似乎更想在這片異國的荒漠中,構建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理想國。
在高速飛奔的當代中國,這比種幾棵樹要難得多。
「苛刻」的日本人
從衛星地圖上鳥瞰,距呼和浩特75公里的白二爺沙壩,總面積12萬畝,就像一個謝頂的中年男人——周邊盤踞著幾綹頭髮,頭頂心依然袒露著大大小小的斑禿。當然,如果沒人來種樹,這裡仍是流沙肆虐的「光頭」。
1982年,當時的和林格爾縣副縣長帶著120名治沙隊員進軍白二爺沙壩。15年後,增田達志也在這裡扎根。
與能在沙漠中修路運水的國家級項目相比,增田採用的是「窮人旱植」的辦法。他雇了數十個村民幫忙,形成一支民間治沙隊。
這位身材不高的中年人一絲不苟地示範。他用鐵锨撥去表面的干沙,深挖一個80公分左右的坑,再把沙柳條插好,蓋上富含水分的濕沙並踩實。
在一位當地村民的印象中,日本人種樹嚴謹得近乎刻板。當年她每種完一片樹,就必須接受抽查——沙土的濕度夠不夠,樹苗會不會輕易被拔出來?基於此,增田的治沙隊每種10棵楊樹,至少能活8棵。
「一個日本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把中國人民的治沙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有人調侃道。
1992年,26歲的增田達志加入遠山正瑛——一位遠赴中國治沙近十年的先驅組織的綠化協力隊,來到內蒙古庫布其沙漠腹地恩格貝。
「那是一個隨心所欲的年紀。」增田回憶說,當他第一次來到中國的時候,不會說漢語,也不懂該怎麼種樹。
「但我喜歡沙漠綠化的工作,喜歡這裡的人。」增田說。在恩格貝,他結識了後來成為他助手的當地人喬二。這對搭檔從一開始就夢想著能有一片屬於自己的治沙基地。有一天,他們從呼和浩特出發,騎著摩托車,灰頭土臉地來到白二爺沙壩。增田覺得這正是他夢寐以求的地方——沙地面積不大不小,本地人還都會種樹。
在當地政府的見證下,1997年,增田與和林格爾縣治沙站簽訂了協議。他分到的沙漠位於白二爺沙壩的腹地,那裡當時連路都不通。此外,買麥秸、買樹苗、僱人工、水、電、房租……所有經費都要自理。
最初幾年,增田每年要在中國待七八個月,剩下的時間回日本打短工。他幫朋友蓋過房子,在大街上賣過關東煮,直到湊夠來年的治沙經費。
每當他從日本歸來,老鄉們總是親切地問候:「回來啦?」
增田就一個勁兒地「哈伊哈伊(中文意為「是」)」。
烏托邦裡的死循環
那是一次艱難的選擇。增田最終結束了在日本從事管理諮詢的白領生涯。
如果只是為了種樹,那麼他的工作在最初幾年就已完成。實際成活的楊樹7萬多棵,沙柳10萬多棵,植草3000餘畝。
「但這些只是沙漠綠化的第一步。」增田跪坐在沙地上,興奮地闡釋他的B計畫——他試圖在這片沙漠裡建立一個可持續的生態體系,讓食物、能源和經濟在社區內實現循環。
在這個有著天葬傳統的地方,沙漠曾被認為是人類回歸自然的歸途。然而隨著環境的惡化和現代文明的衝擊,這種「水、草、人、牛、羊」的共生關係早已不復存在。
增田試圖在他的理想國裡重啟人與自然的操作系統,他雄心勃勃的計畫包括:
——租100畝田地,嘗試種植南瓜、土豆甚至日本人愛吃的牛蒡,以探索適合當地氣候的農產品。
——幫附近的牧民挖沼氣池,引進太陽能產品,利用風能發電。
——從老家引進享譽世界的神戶肉牛,用原生態的方式放養,在呼和浩特乃至北京、東京建立銷售網路。
增田隨手在沙地上畫了一個循環往復的三角形——牧民利用綠地養牛,牛產生經濟效益,錢和牛糞回饋這個沙漠。
他的宏偉計畫一度往前邁了一小步。增田認定,本地人的參與能從根本上防止再度沙漠化。幾年前,增田的治沙基地與鄰近的兩個村子簽訂協議,由此達成的第一項決議也是個三角形——村民幫忙修剪楊樹的枝條;樹葉拿去餵羊;楊樹會長得更快更高。
然而事實是,村民們從未修剪過枝條。如果有外來的志願者這麼做了,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把羊趕來,吃掉樹葉,再把枝條搬回去燒火。正如他們每天在這片沙漠裡放羊,卻從不遵照協議在裸露的沙丘上補種些草。
「增田總是不理解,但我理解。」助手喬二說,「如果得不到利益,沒有人會和你想法一致。」
失落的世界
「日本人的想法挺好,可我沒時間。」50歲的高秀女有些抱憾地說。
過去,她們一家都參加了增田的植樹工作。但從她的描述來看,那僅僅是一種雇佣關係。似乎除了村子不再飽受風沙之苦,這個遠道來治沙的日本朋友並沒有改變她的生活。
這個以「32號」為名的村子地處白二爺沙壩的邊緣地帶,過去有20多戶人,如今只剩下10家。像這個國家的大多數村莊一樣,留守的都是婦女和老人。
高秀女的幸福生活不在這片沙漠,而是濃縮在掛滿一整面牆的相框裡。兩個兒子在呼和浩特買了房,一個做包工頭,另一個在餐館做廚師。當福建人來到白二爺開石礦的時候,其中一個年輕人與她的女兒相愛了。廈門海灘邊的照片透露,女兒和外孫已經過上了有車有房的城裡人生活。
只有她的老伴還在外省幫人蓋房子,農忙時才回家看看。
沙漠就像一座圍城,有人想衝進去,有人想逃出來。過去十多年來,高秀女和她的家人們都在極力追隨這個國家工業化和城鎮化的腳步,逃離這個荒蕪的村莊。
「他們會想,白二爺是沙漠或是綠洲,又與我何干呢?」曾經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的志願者王仲青說。
試圖恢復田園牧歌的增田達志,如今將要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失落的世界。
「白二爺是我的家。」增田不止一次這麼說過。
增田是從一個飛速向前奔跑的國家「逃」到這裡。他出生在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期,每年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增長10%以上。在增長奇蹟之後,日本的經濟危機、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交織迸發。
1997年1月,增田在日本成婚,兩個月後夫妻倆就在白二爺基地租房安家。他把這裡看成是理想生活。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放開飛奔的腳步,也沒有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沙漠腹地的現代化生活就只有一個電燈泡,沒有下水道,沒有浴室,沒有廁所,但增田覺得每天都過得很快樂。十多年後,沉浸在回憶中的增田說:「那時簡單的生活,從此改變了我對待生命的態度。」
喬二請辭
「他是我的兄弟。」在一篇向日本朋友介紹助手喬二的博文中,增田想起了19年前與喬二初次見面時的情景。語言不通是讓博士也撓頭的難題,好在兩人都好喝酒,對飲了兩打啤酒後就都失去了知覺。
4月15日這天,喬二花了4個多小時,徒步走遍了兩人共同改造過的所有沙地。
「我們15年的工夫沒有白費。」他喘著粗氣對增田說,看著大自然的傷口正在恢復,「心裏真痛快。」
喬二是在向他的兄弟和過去道別。
這一天,喬二正式向增田提出辭職。因為大兒子眼看就要上大學了,隨後是娶妻買房。他試圖向增田解釋,這是每個中國父母都面臨的巨大壓力。儘管幾年前,增田支付給喬二的補貼從每月1000元漲到了2000元,但畢竟,這是一份沒有勞動保障的工作。
「我並不想離開,多年來我一直想幫助他完成這個事業。」喬二搖著頭說,「可是沒有辦法。」
資金一直是增田治沙的短板,據他計算,個人投入加上志願者們的捐贈,15年來累計花費了大約400萬元人民幣。
增田的下一步計畫是去中國第七大沙漠庫布其開闢新的治沙基地,然而沙漠的承包價格在近10年來已翻了300倍,到了他無法承受的地步。
有錢人正在投資沙漠。是為了資源礦藏還是旅遊開發?隨便吧,只要錢能生錢。過去他們開發草原,現在終於開始在沙漠淘金。
從沙漠回到北京,站在最繁華的CBD國貿附近,增田達志指著那些高樓直言不諱地說:「我不喜歡這裡。」
每次前往植樹的地點,增田都會經過「32號」村旁福建人開設的那個採石場。「運載著幾十噸巨石的大卡車使得連接村莊和小鎮的道路變得異常難走,爆破聲震碎了村民的窗戶……」
按照社會學家的觀點,正是現代人過度消費的生活方式和無節制的工業開發,共同造就了增田所看到的那個失落和貪婪的沙漠世界。
增田明白,開發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村民們在礦上打工的收入很快將不復存在,留下的只有坑坑窪窪的荒地,泥濘不堪的道路和泥土碎石堆積而成的危險的小山。
在送別北京志願者的那個晚上,增田喝多了。他站起來嚷道:「每個人都有故鄉。我想為大家唱一首關於故鄉的歌。」
增田說,他的妹妹就住在日本福島,離核電站不到20公里,2011年因為地震和海嘯,準確地說是因為核泄漏,妹妹一家被迫離開了家園。
這位在中國待了近二十年的日本人其實一直在思索,讓人們失去家園的究竟是大自然的偉力,還是我們自己?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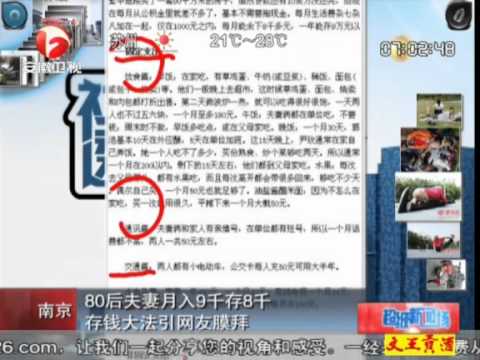




排序